发布时间:2018-08-20 来源:安徽作家网 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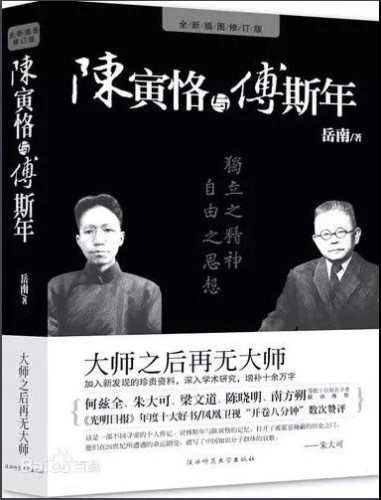
传记纪实《陈寅恪与傅斯年》
岳南著
推 荐 人 语:
文人两种
董改正
读岳南先生《陈寅恪与傅斯年》是在我旅居海南,台风过境时,飘窗外风狂雨暴,内心也是狂风暴雨。岳先生的文字,井然凛然,亦磊然快然,全书情绪饱涨,节奏把控极好,或长焦距,或微镜头,或快进,或慢写,或有金铁之声,或呈汪洋之势,或山花烂漫,或钟鼎齐鸣,思辨与叙述并重,理性与感性并呈,此书的阅读是我绝无仅有的一次发蒙式体验。
究其原因,并非故事的精彩,而是作者选择的传主极有代表性,一个是读书种子,“三百年来仅此一人”的“教授的教授”;一个是“人间最稀有的一个天才”,开创风气、创立制度的文化闯将。虽然性情截然不同,人生履历大不相似,但相同的地方在于,二人皆有陈寅恪为王国维所撰碑文中所述的“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都有纵使俗世滔滔,吾当洁身自好的赤子情怀,两人都把文人做到了极致。
寅恪先生是江西修水人,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兄长陈师曾,祖孙三辈同列《辞海》四个条目,中国史上除帝王之家外,可说绝无仅有。先生学术精深,为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在历史研究、新考据学、区域文化、宗教语言、诗文等方面均有突出贡献,其治学精神影响深远,其研究方法如“以诗证史”等更是成为一种历史研究的新方法。寅恪先生以其极具想象力、创造力的学术成果开创了中国现代史学的新疆域。
先生兢兢于教学,敦厚于为人,提携扶掖,谦逊温润,然在教学之上,先生却很自负:“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是以先生课上学生云集,学生中有他的诸多同事,如教授朱自清、冯友兰、吴宓等。冯友兰先生每每恭陪寅恪先生步出教员休息室,坐到教室后排听课,下课时,垂手立于教室门口,等先生先行,俨然执弟子礼。桀骜不驯敢大骂领袖的刘文典,对陈寅恪却是“十二万分的佩服”,有人质疑陈寅恪,刘文典立即破口大骂。
而作为“人间最稀有的一个天才”(胡适语)的傅斯年,却是一个“磅礴”的山东大汉,其膀阔腰圆,形如小山,精力充沛,思维迅疾,行事果敢,霸气四溢,颇似梁山好汉,外号人称“傅大炮”。一次蒋公问:“孟真岂不我信?”傅斯年慨然答道:“不是不信校长,是不信校长相信的人!”某次浙大在史语所挖人,教育部已经发文,但傅斯年拒不放人,蒋梦麟、刘大白联名发电给傅,命“速予放行,勿再留难。”傅斯年大怒,于百忙之中复电大骂,其言纵横磅礴,纵使时逾百载,气息犹可闻也。
“其才则天才”,但傅斯年一生所遗著作不多,原因在于,他的精力主要用在诸如创立了“史语所”和“台湾大学”这样的学术和教育机构之上,先生行事但求无愧于心,一俟决定,一定全力以赴,想尽方法一往无前,逢山开路遇水搭桥,遇到神魔他必举起巨斧大喝一声冲杀过去,一般都是三军辟易。
两位先生惺惺惜惺惺,相互支持,互为倚靠。尤其是傅斯年对陈寅恪,更是在最艰难的时候,为他的生活和学术研究提供了他竭尽所能的帮助。二人友谊,反转了“文人相轻”的论调,令人心向往之。
两位先生将文人的两种模式演绎到极致。二人皆有冰雪品格,皆不随流俗,皆有独立自由之思想。陈寅恪先生在几乎断粮的情况下,几次拒绝在日伪盘踞区任教。而傅斯年先生,也将嶙峋傲骨挺立一生,一生不加入国民党,为的是“一入政府,(学界)没人再听我们一句话。”敢在蒋介石面前翘着二郎腿、叼着大烟袋,跟蒋指手画脚的,举国民党上下,唯孟真先生一人而已矣。做学术则甘守清贫寂寞,绝不上蹿下跳,只为“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做事则廉洁奉公、秉持公正,不畏权势,虽万人吾往矣。两人承接前辈学人风骨,立起后世典范,为我们这个风云变化的时代之文人何去何从,指引了方向。
岳南先生的这部作品,史料详备,观点明确,有寅恪先生考据的精微,也有孟真先生纵论天下的豪情,是一本可以佐酒的“豪书”。我虽读过几本书,有些书的经典程度和文本价值远远大于此书,有很多书足以影响我的人生观,但这本书却形象而非说教的呈现了两种我所崇敬的文人范式,让我明白,一个人之所以能被尊敬的,一定先是他的品格;一个人所以能“成其大功”,一定是个特立独行的人;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一定要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精神”。对于一个读书人来说,尤其如此。因为软糯的文人,远不如诚实的农民有用,而其破坏性却远大于之。
很多年来,我一直记得海南的那场雨,记得我在极度困难中读的这本书,它让我在极度的贫窘中,犹自不敢放弃底线,不敢自甘堕落。一旦有随波逐流的想法,眼前就会出现寅恪先生温和而清澈的面容,和傅先生戟指怒骂的表情。
推荐人:董改正

董改正,安徽铜陵人,1975年生,有若干散文发表于国内报刊。
(“作家荐书”栏目欢迎广大作家朋友推荐自己正在阅读的书籍,来稿请寄ahzx1971@126.com 注明:“作家荐书”字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