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9-11-21 来源:文艺报 作者:林培源 陈润庭

林培源,1987年生,青年作家,广东省汕头澄海人,现为清华大学中文系博士生,美国杜克大学访问学者。曾获得两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以及第四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短篇小说佳作奖等。小说作品发表于《花城》《山花》《大家》《作品》《青年文学》《小说界》《江南》《长江文艺》等文学期刊,已出版长篇小说《以父之名》、小说集《钻石与灰烬》等,2019年出版小说集《神童与录音机》。
陈润庭:在当下,文学越来越面临来自各方面的挤压和冲击。一方面是网络文学已经成为大众文字阅读的主要内容与方式;另一方面,严肃文学有沦为边缘的“圈子游戏”的危险,大家自说自话,自我满足。诚然,上世纪80年代建立起来的文学期刊之间松散的“等级制度”还在暂时发挥作用。作为今天的写作者,依旧选择在纸质文学期刊上发表作品的意义是什么,已经成为了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林培源:在文学生产体制中,文学期刊是不可绕过的一部分,不管是现代文学还是当代文学史上,文学期刊杂志以及编辑、发表、出版和流通的过程,形成了一个巨大繁复的文学场,作家的创作和读者的接受很大程度依赖于这样的体制。你说的严肃文学的危机,前提是文学流通和接受或者说阅读方式的转变之。新媒体(微博、微信等)和网络文学相辅相成,一方面改变了我们传统的“纸媒发表—读者购阅”的流通方式;另一方面,也为传统的文学期刊带来新的面貌。以前很多报刊亭会销售文学杂志(当然也包括其他娱乐杂志、科普杂志等),读者会在报刊亭购买阅读,但是现在报刊亭越来越少,一些文学期刊渐渐缩到了图书馆、机关单位或者研究机构,沦为“专业读者”阅读和批评的对象。当然,现在网络很方便,我们也可以通过订阅文学杂志的微信公众号获取相关信息,这其实也形成一个新的“朋友圈”文学生态。在我看来,文学发展到今天确实遇到很多挑战,期刊的发行量在减少,网络文学、新媒体在膨胀……尤其在这个全球化时代,中国读者也可以实时通过网络读到西方报刊发表的文学作品,及时了解世界文学动态——这是信息时代的便利。不过我想从另一个角度回应你说的“严肃文学的危机”。
结构主义批评家托多罗夫有本书叫《濒危的文学》,作为一个经历过前苏联和东欧体制的过来人,托多罗夫所谓的“文学的濒危”也可以理解成是某种文学的危机,只不过这个危机是在特定的历史形态和时期出现的,托多罗夫当然更看重的是文学本身的复杂性、丰富性。这是托多罗夫的现身说法,值得我们借鉴。文学在一个后革命的时代,在一个消费主义、物质主义大肆渗透进日常生活的时代,如何保持其独立性和尊严,恐怕是每个真诚的写作者必须面对和思考的。文学期刊当然很重要,但并不是唯一的载体。在这样一个时代,只要你想写,随时都可以找到平台发表,我们当下也有许多契机可提供给年轻的写作者,比如连续举办了20年的新概念作文大赛、《收获》杂志推出的“青年作家专辑”、《鲤》杂志的“匿名作家”写作计划、“宝珀”理想国文学奖等等。
陈润庭:可能因为“出名要趁早”,我们很急于“收割”青年作家。现在有很多提供给青年写作者的赛事,帮助优秀的青年写作者冒出头,这当然是好事。但是不是每个写作者都会在青年时期展露才气呢?我觉得不一定。很多中年的写作者,或许名气不大,但读他们的作品时,我总是肃然起敬。他们作品中的气息与漫长的自我精神成长是分不开的。但我们的现实却是,如果一个写作者错过了年少成名的班车,又不在高校、杂志社等机构任职,那么他的写作似乎就注定了不为人知的命运。张定浩在早前的访谈中,曾说我们“现在对所谓的年轻一代写作者越来越宽容”。歌坛有个说法叫“歌红人不红”,但很多年轻的写作者或许已经获得了文学奖的嘉许、文学界的关注,却陷入了“人红文不红”的窘境。
谈谈文学吧,如你所说,在这个时代,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写作者,作品也不存在发表不了的问题。由于网络平台的影响力,很多严肃文学的作者将自己的作品放到豆瓣、微信公号等平台发布,有的阅读量可观,但大部分都只有可怜的阅读量,或许这正说明严肃文学的危机看似始于网络,但并不因为媒介的跟进而消失。某种狭义上的文学正在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退场,而看似与文学没有密切关联的领域,比如电影、二次元等,也渐渐进入写作者的视野。可喜的是,文学因为走出了纯文学的藩篱,借力打力,重新获得了某种生命力。但事实上,在各股力量争斗的角逐场中,以笔为生的写作者是“资本”最薄弱的一员。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文学作品改编电影,原著往往成了一个空壳子。文学在当代文化生产中,成了初级的原料提供商,生产故事,生产戏剧冲突,但并不产生价值,更不具备社会批判的功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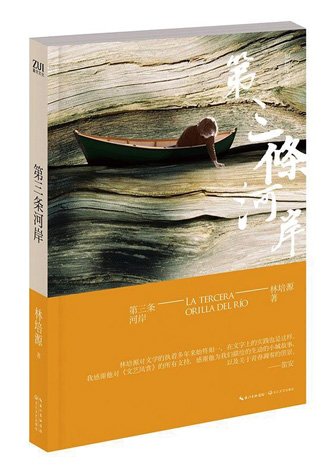
林培源:你观察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拿豆瓣来说吧,有的写作者一开始默默无闻,习惯了在“无名”状态下写作,但写作某种程度就是在暗中寻找读者,所以他们会把写好的文字贴到豆瓣上(不管是小说、评论还是其他体裁的文字),渐渐就引起了一些读者的关注。有一类豆瓣“网红”作家就是这么走进读者视野的。这也是一种野蛮生长、最终进入主流文学视野的现象。他们当然也会在纯文学期刊发作品,同时在网络上凝聚了大量的拥趸,这样就反过来引起了主流文学界(这里指的是上个问题谈到的传统文学生产体制)的注意,再被收至“麾下”。我当然也认可文学变得越来越小众和专业化的说法。这个问题之所以不可忽视,是因为在当今社会每个人面临的诱惑越来越多了,金钱、名声、权力……2007年我参加第九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当时认识了不少写作的同行,但是12年过去,坚持写小说的人寥寥无几,大部分都奔向其他行业了,有的或多或少还干着和文字相关的工作,比如编剧和影视行业;再者,面临大众文化(电影、动漫等)对文学空间的挤压,写作者会试着从这些领域里汲取一些营养,试图去拓宽创作的边界,比如有的人会借鉴赛博朋克电影(《银翼杀手》等)的元素写科幻小说,甚至将科幻电影中的一些世界观和元素引入小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现象,关键还是不能颠倒了其中的边界,小说最终还是要写出小说本身该有的东西,也就是所谓的“文学性”,不能沦落为对其他文类蹩脚的模仿。
陈润庭:你说“小说最终还是要写出小说本身该有的东西”。米兰·昆德拉也有相似的说法,他说“小说唯一的存在理由是说出唯有小说才能说出的东西”。但说出唯有小说才能说出的东西并不简单。当代的各个艺术门类面对着同一个时代,当代的艺术创作者也面临着某种“最大公约数”的存在境况。在这种情况下,小说要保住自身言说的活力,不沦为其他艺术门类的原料提供商,可能必须重视先锋的作用。先锋已死是老掉牙的议题,就连“80年代式的先锋文学不会再有,但写作永远需要先锋精神”,也只是老掉牙的空论。皮埃尔·布尔迪厄在分析文学场域时,说过先锋派其实也分被承认的与不被承认的。当先锋派被承认时,恰恰说明其先锋性已经成为历史。先锋既是恒在的,又是面目不断变化的。短篇小说集《神童与录音机》“先锋性”的体现,依靠的不是骨架嶙峋的叙事形式,而有赖于城与乡两种经验的对垒与互渗。有时候我很怀疑,当下文学正在发生的先锋派,是否还在严肃文学批评家和作者的视野之中。
林培源:你讲得很好,不同时代的文学总有一个参照和反驳、对抗的对象,比如上世纪80年代的先锋文学。先锋文学的产生,一方面是从纵向的历史上对此前文学观念的反拨,另一方面从横向上又是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互相交融的产物,莫言、余华、苏童、格非,他们都是在世界文学尤其是拉美“爆炸”一代文学的滋养下成长起来的,你说的“承认的过程”实际上从文学史来看,也就是一个被逐步经典化的过程,被写进了文学史,好了,你就被定性了,被供上了神龛供读者瞻仰、研究者研究。顺着这么一个文学史的逻辑和脉络看下来,我们这个时代的“80后”“90后”写作者和上世纪80年代的先锋文学相比较,似乎变得越来越没有先锋精神,稍微浏览一下文学期刊,会看到太多庸俗、无趣的小说。怎么无趣呢?就是讲一个圆滑的、自圆其说的故事,但是小说内在的精神含量浅薄得可怜;当然也存在另外的“野生作家”,他们蔑视陈规陋习,实践着文本形式上的新颖,甚至践行着一些跨文本和文类的实验,以此显示他们的叛逆精神。这当然是好事。但我在写小说的时候,更多希望能在文本结构、形式和故事之间做一个调和,不完全拒绝讲故事,但也不是奔着花里胡哨的形式而去,就像2016年我们做过的一个访谈,题目我至今仍很喜欢——《我想避免“平庸”的现实主义》,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陈润庭:每次读到这种“平庸”的现实主义小说,我都要花点时间平复心情,尤其是看到作者还是年轻人的时候。最后我想聊聊文学代际的问题。作为文学制度的一部分,文学代际的划分有利于创作群体的推陈出新,以迭代的形式,保持文学的活力。“80后”作家在一开始便以爆炸式的姿态出现,引起诸多争议。而“90后”作家则在“期待叛逆”的目光下登场,反而显得乖巧温驯。你怎么看待与你同代的写作者,以及他们的写作?
林培源:近几年不少文学期刊推出了“90后作家专辑”,一些新鲜的面孔悉数登场,文学生态看起来比从前更繁荣了,可实际情况真是如此吗?很多年轻写作者确实在“期待叛逆”的目光下登场,但总体的姿态却是乖巧温驯的:他们很懂得批评家需要什么,读者需要什么,他们很精明,知道怎么迅速地登上舞台,那里有聚光灯打下来。这样的情况也不惟“90后”,我们看到其他代际的作者写到一定程度就疲乏了,作品中那种早年就该有的气力褪去了,小说语言越来越油滑、松散,没有生气,写小说变成了一个熟练的手艺活。这也是我自己要警惕的。和我同代的作家中有不少佼佼者,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不少东西。我有一个不成熟的看法是:小说最终构建和体现的是写作者的文学观。因此要进步,除了保持对日常生活的兴趣和持续的观察、思考之外,恐怕阅读还是一个秘密武器,在阅读中加深对世界的理解,重塑新的经验,或许才能越写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