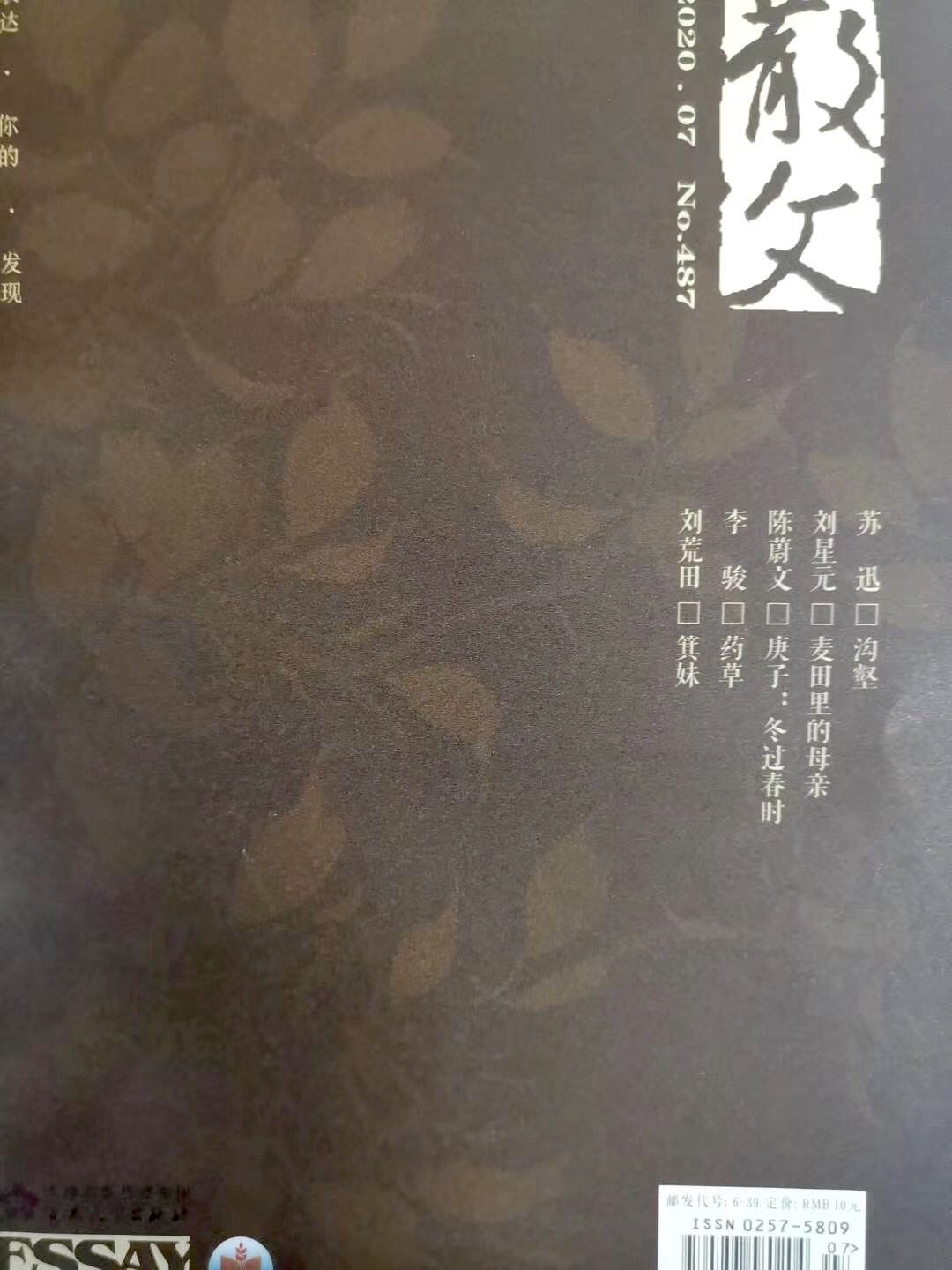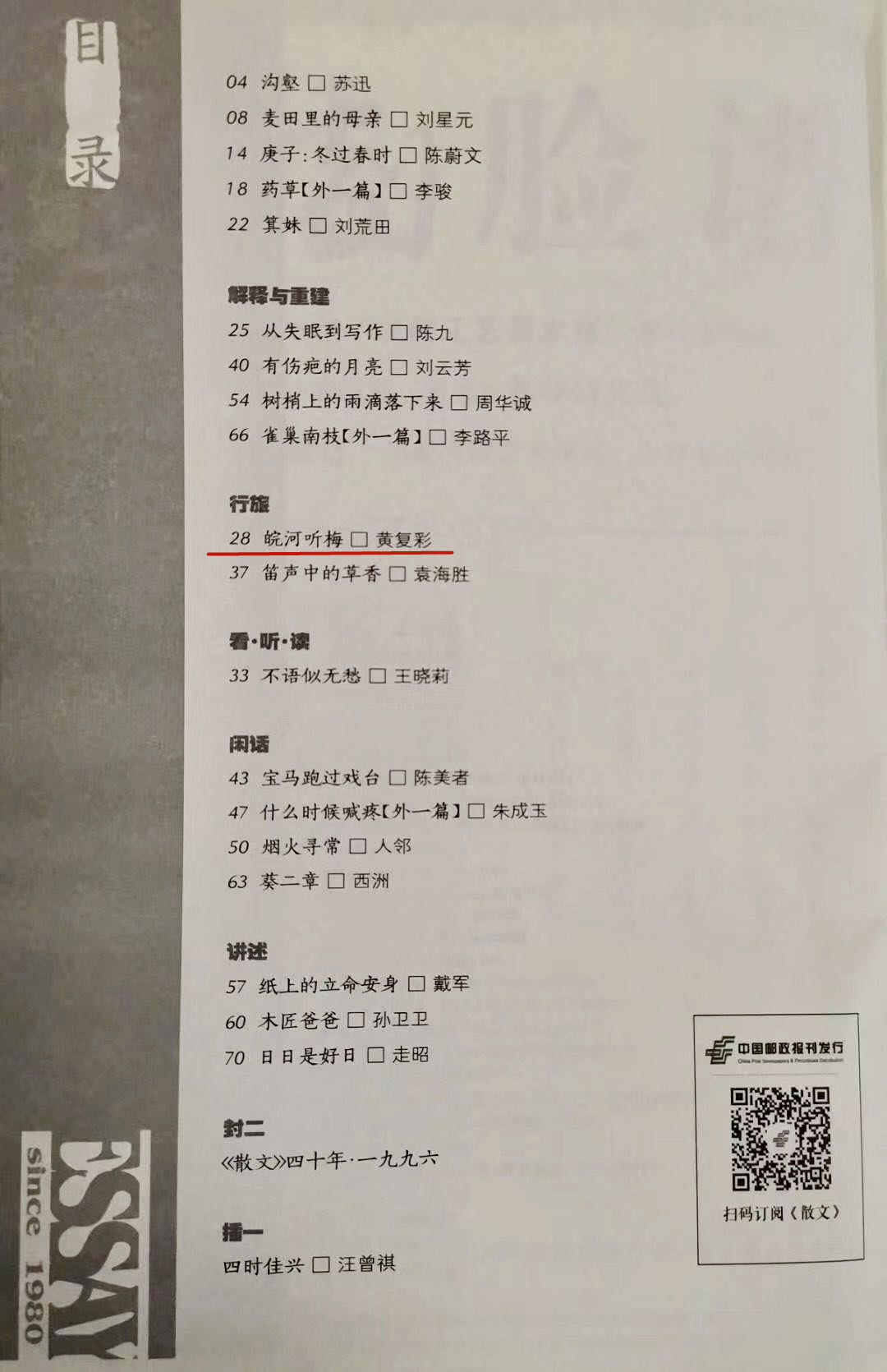皖河听梅
黄复彩
戏乡记
到石牌来,原是要看戏的,然而却没有戏。但我走在石牌的大街小巷里,听到的每一个声音都是软糯的黄梅戏道白,看到的每一个老人都是我熟悉的某一个人。
我的初中语文老师江孝明先生就是这一带人,直到前年,我去看他,离开家乡六十余年的老人,依然用纯正的方言同我回忆着五十多年前的一桩桩事情。他在说那些事时,他的夫人就一直站在他的身后,微笑地看着我们,好像在说,你看,他的记忆力有多么好。她是一位曾经的黄梅戏演员,我在幼时曾看过她的演出。江老师客厅的墙壁上挂着一把琴杆呈暗红色的老式二胡。我想起他傍晚时分坐在教师宿舍门口拉着二胡,沉醉在二泉映月乐曲中的情形,想象着他与退休后的夫人琴瑟相和的幸福场景,真是为老师有这样的晚年生活而高兴。
怀宁县城撤走后,石牌镇一下子冷清起来。然而它曾经的风景还在,旧日的繁华还在,现在,它像一个暂时落泊的汉子,只静静地守着祖宗留下的一切,等待着一个时机的到来。
我们走进街边的一间书屋,墙上的书法作品每一幅都是欹欹斜斜,醉意欣然,却也各有情趣。坐在门口晒太阳的老者气定神闲,他仿佛在告诉人们,他经历过,喧嚣过,就像一条溪流,一路高山大河,终于归若沉寂。现在,他守着他的书屋,案上墨迹未干的书法随性所至,喜欢与否,任由他人。对于走进他书屋的我们,他似乎有一种生逢知己的欣慰。他乐意为我们书写一幅幅郑板桥式书法,并热情地与我们合影留念。我很想请他唱一段黄梅戏,他中性的嗓音,还有他一脸的沧桑应该很适合《江水滔滔》那样的老生唱段:
“江水滔滔向东流,儿的日子才开头,(你)好似那水面上的浮萍草,风吹浪打随水流,儿啊……”
书屋的隔壁是一家制作戏服和皇帝冠冕的铺子。搁在案台上的冠冕每一顶都珠光宝翠,两旁的大红流苏垂落下来,丝绦上吊着的玉佩就像真的一样。我试着戴了戴,门口晒太阳的妇女一起说,他戴着真好看。我把冠冕取下来,放回案台上,我知道我戴着并不好看,我的脸型我的气质都不适合戴这个。我当然也是不会买这个回家的。我问他这些戏服和冠冕是否卖得出去,他爽快地说,好卖着呢。他告诉我,在这样的年头岁尾,盖房建屋,修志拓碑、红白喜事,附近的乡镇几乎每天都要唱戏,戏台就现成在祠堂屋里,或直接就搭在田间地头。
清代学者包世臣《都剧赋》说“梨园佳子弟,无石(牌)不成班”。那一天包世臣来怀宁参加大书法家邓石如的一个祭日,顺便来石牌看当时被称为“采茶调”的地方小戏,正值黄梅时节,石牌家家有戏,处处搭台,包世臣大发感慨,遂改宋人赵师秀《约客》诗中“黄梅时节家家雨”为“黄梅时节家家戏”。石牌人认为,“黄梅戏”这一流传至今的剧种就是这样诞生的。石牌出戏,也出人。杨月楼、程长庚这样在中国戏剧史上大名鼎鼎的人自不必说,明末的戏剧家阮大铖就生活在这附近一带,《明史》明确记载他是怀宁人。但阮大铖的名声不好,先依东林党,后投魏忠贤,只为心底里的那一片幽暗,可他要依投的,哪一个又是什么好东西?于是,不屑与他为伍的怀宁人便说他是桐城人,桐城人当然不买这账,仍说他是怀宁人。但说他好也罢,说他坏也罢,他的戏剧,却是美的,这一点,就连骂他的人都不得不承认。
少年时从破四旧的故纸堆中拾得一本线装书,无封无底,无头无尾,那时正无书可读,便半懂不懂地读了起来,正当我被书中一男二女的爱情逗得血脉贲涌时,却被对门一位老大强行借去,竟再不归还。过了半年光景,对门却在腋下夹着一个纸包悄悄来到我家,除了那本失而复得的线装书,还有一本朱生豪译《莎士比亚戏剧集》,他说他父亲决不允许他读这种封资修的东西,只好先放在我家。我不明白他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却为自己沾了便宜,一本得两本而暗自高兴。过了几天,对门家里被几个戴着红袖章的人抄得个底朝天,也不知道抄走了一些什么。事情过去之后,我把这两本书再送给对门老大,但他说,你帮助了我,我不能报答你,这本《燕子笺》本来就是你的,《莎士比亚戏剧集》就算我送给你的吧。我自然又是一阵高兴,只是,这两本戏剧集,一中一西,一喜一悲,连同家里其他的书,都在下放农村前夕被我一文不值地卖到了废品收购站,却不知道是悲剧还是喜剧。
在程长庚故居,我们在他的铜像前合影留念。高高的花岗石基座上,程长庚手握折扇,眺望远方,却像是大有忧国忧民。顺着他的眼光看去,远处的长河与潜水的汇合处波光潾潾。再远处,是一道又一道青山在虚淡的青烟中若有若无。从他的“故居”里传来伍子胥的一段西皮流水:“过了一关又一关,心中好似乱箭穿,腰中枉挂三尺剑,不能报却父母冤……”这段苍凉沉郁的唱段让我想起少年时代老家里的那个敲着鱼皮鼓,用同样苍凉沉郁的嗓音说大鼓书的瞎子长明。想起长明,那段同样苍凉的岁月便像鱼鼓一般在我的耳畔清晰起来。我遂明白,人生的戏剧,只有到了我这年纪时才能品咂出一些其中的滋味。人都说人生如戏,或喜或悲,究竟起来,那所有的喜剧都是悲剧,那所有的悲剧都是喜剧,人只在其间扮演着生旦净末,是扮给人看,也扮给己看。
有一段时间,我疯了般的只想去报考黄梅剧团,如果不是父亲以打断我的腿相威胁,说不定我真的去做了一名蹩角的演员。没有人知道我内心的秘密,那时候,被银幕上美如仙人般的冯素贞撩拨得春心萌动的少年又何止我一人?直到有一天,我终于在县城唯一的剧院里见到真实的严凤英。虽然只是看到一截不花钱的“放闸子”戏尾,但舞台上的严凤英身穿大红毛衣,迭得整齐的白围巾优雅地搭在脖子上,她站在一片青松之下的凛然之美让我感动得无以复加。
我们要离开石牌了,忽然,从附近一家店铺里传来韩再芬黄梅戏《小辞店》的一曲唱段:
往日里回店来笑容面带,
今日里为什么愁眉不开?
解不开其中意打坐哥哥一块,
蔡郎冤家心腹上的哥,
哥哥啊,奴家的哥,
有什么心腹上的话对妹妹说来……
我被这段唱词打动了,站在那条被冬日的阳光铺满的街道上,竟至于迈不开步子来。
十二月花神
正月梅花开
渡春江,点缀好时光
冰肌玉骨映红妆
孤山留素影
独占百花王,百花王
二月杏花开
满园栽,独自出墙来
千红万紫巧安排
酒家何处在
春雨杏花飞,杏花飞
……
这是潜山县五十年代就开始风靡城乡舞台上的一曲歌舞调《十二月花神》中的一段。那天我们去三县交界处的潜山,在黄泥镇文化馆,竟意外地得到这首曲调的全部唱词,也算意外中的意外。郑蔚老先生是我三十多年前的一位作者,当然是他先认出了我。他说大约十年前我们还在报社见过一面。如果不是他说到《十二月花神》,我还真认不出他来。作者太多了啊。
安庆第一届黄梅戏艺术节,我作为剧组工作人员,有幸坐在剧场的第一排正中位置。那一届艺术节展演的并不都是黄梅戏,譬如望江的《挑花舞》、太湖的《花梆舞》,以及潜山黄泥镇的《十二月花神》。印象最深的当然就是这《十二月花神》了,我记住了零零星星的唱词,也记住了那十二位打扮得异常俏丽的女孩子在舞台上的婀娜多姿。有着三百多年历史的《十二月花神》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皖河人奉献给这世界的艺术,它的魅力是隽永的。我就是在那以后给郑蔚老师写信,请他帮我弄到一本《十二月花神》的曲本。
十月芙蓉开
绿满阶
滴露点尘埃
芙蓉帐里凤鸾谐
花枝轻弄摆
迎接曼卿来,曼卿来
……
我读着这些美艳而节律分明的歌词,郑蔚当年的形象也逐渐在我的脑子里清晰起来,清晰成我们彼此曾经的岁月,以及黄泥镇一段段泛黄的历史。
一千多年前,皖河得天独厚的水上交通造就了一个个皖河小镇,而位于潜山、太湖、怀宁三县交界处的黄泥镇则有“鸡鸣狗吠听三县”的优势。那时候,在黄泥镇做生意的不仅有本地人,更有外地客,郑蔚的文章中就曾写过“河北六家店”,也写过“河南一条街”,当然还有《十二月花神》。
花是人类在艰难时世中对一切美好期待的象征。佛说,人是苦的,这种苦几乎伴随人生命的始终。但是,有了花,人类便不再觉得生命中不可承受的种种之苦。佛用“拈花微笑”开启人类的智慧,“花开花谢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曹雪琴用花来抒写悲剧的人生,屈原用花来传递对君王政治的理想信念。产生于西方的哲学思想泛灵论认为,万物皆有神祇。随着十二月季节的转换,月月都有花神。与其他地方的《十二月花神》所不同的是,黄泥镇的《十二月花神》不仅有女花神,更有男花神。在湘水旁“滋兰九畹,树蕙百亩”的屈原开一年中花神之先,“采菊东篱下”的陶公渊明则夺得金秋时节十一月的菊花之魁。郑蔚说,欢迎你们正月来,那时候或许能看到翩翩起舞的《十二月花神》的花街游行。
郑蔚把我们带到皖河边,正是枯水期,昔日繁华的黄泥镇码头只有不绝于耳的棒槌声,只有成群的老鸹在深潭处翩翩翻飞,它们在寻觅着露出水面的小鱼,或者只是以它们特有的歌舞迎接着我们这些不速之客。失去水上交通的黄泥镇衰落了,打工潮把黄泥镇的年轻人都吸引到外面去了,留在黄泥镇的似乎就只有老人、孩子以及留守的妇女们。
在一条老街上,我们见到陈满秀老人。当时她拄着拐杖站在自家门口,她富态、端庄,这从她的衣着可以看出来,从她手腕上的镯子,手指上的金戒指以及她站在那里一副君临天下的神情中可以看出来。她饱满的额头,手背上看上去富有弹性的皮肤怎么都看不出她是一个年过九旬的老人。我想到我的母亲,母亲九十一时,应该就是这样健康,这样自信,带着一个过来人对一切过往日子的驾轻就熟,还有同样君临天下的大嗓门。
我应邀走进老人的屋子,客厅的条桌子上供着一张发旧的照片,照片上的年轻人五官清秀,面貌俊逸,不管在哪个年代,都能称为美男子。我问陈老,这照片上是您老什么人?陈满秀说,是我老头。我注意到她说这句话时脸上的表情带着几分羞怯,甚至有一丝红润。她说,这是他当年从朝鲜战场上回来时拍的照片。而在另一幅相框中,我看到年轻时的陈满秀抱着孩子,紧挨着她的是她年轻帅气的丈夫。她指着一张张发黄陈旧的照片说,这是当时去朝鲜探亲时拍的,这是在丹东,当时我过不去,他只得请假过来陪我,当天就回去了。夫妻俩这样聚少离多的生活一直维持到板门店谈判结束,但丈夫还是没有立即回到国内,而是留在朝鲜,留在他的岗位上。直到一九五六年,丈夫回来了,回到镇上的供销社担任会计,而她则是在一家杂货店当售货员。这是一个让镇上人人向往的家庭,一对让人羡慕嫉妒恨的夫妻。三十多年前,她的丈夫死于癌症。陈满秀老人眼里噙着泪花,一边动情地说着她的丈夫,说他的好性格,说他的多才多艺,她不时地撩起袖口,揩擦着丈夫镜框上并不存在的灰尘。我想,她一定又回忆起丈夫年轻时拉着二胡,夫妇俩在皖河岸边一起唱十二月花神时的情形吧。
显然,她为自己在这个漫长的白日能找到一个倾诉的对象而高兴。她把我们带到她的后院,狭小霉湿的小院里杂乱地种着几盆菊花、一二盆月季,还有几盆凋谢了的二月兰以及月见草等。一只废弃的水缸里,四季桂正散发着淡淡的幽香。我称赞她的花种得好,她兴奋起来,说,先生我给你唱一段《十二月花神》吧:
九月菊花黄,闹重阳
晚节倍留香
天生傲骨斗残霜
东篱新菊酿
莫负好时光,好时光^……
她的嗓音老了,旋律是粗糙的,没有高音,也没有低音,只有简单的几节音符,但她口齿清晰,我听清了每一个字符。我相信,她年轻时一定在黄泥镇的大街上演过《十二月花神》,或许,在1954年上海华东地区文艺汇演舞台上,也一定有陈满秀花枝招展的舞影。
我们走出很远了,回过头来,看到陈满秀拄着金属拐杖站在那里,仍然以她君临天下的姿态看着我们,看着这条她生活了九十一年的大街。我突然有一种冲动,我想停下来,摘几朵路边人家花盆里的花,扎一只花冠送给她,送给陈满秀,送给这位像我母亲当年一样健康的不老的花神。(完)

黄复彩,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长篇小说四部,散文集六部,先后在《人民文学》《散文》《读者》《清明》《安徽文学》《江南》《青年作家》《滇池》《雨花》等杂志发表各种文学作品六百余万字。其长篇小说《红兜肚》为中国作协重点扶持作品,获安徽省政府最高文学奖一等奖。2018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墙》为安徽省作协重点扶持项目,获安徽省政府社会科学奖文学类二等奖。散文集《让自己的心明亮起来》为“当代青少年必读的精品美文”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