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0-09-17 来源:安徽作家网 作者:李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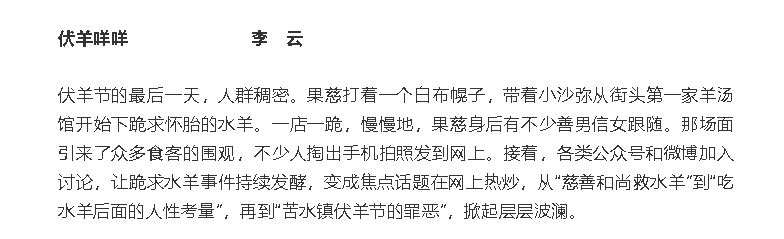
四
苦水寺的香火又盛起来。乡人都说归功于果慈的到来,果慈却说这归于苦水寺里那口神奇的井。
据传明洪武年间先有了苦水井,才有了苦水寺。苦水井井水终年溢出井沿,是股活泉水,但井水苦涩,平日里没有人去饮用,但一有得道高僧来临就有甜水涌出,甚神奇。慧普在世时,苦水井涌汩甜水,慧普去,甜水绝。果慈升座,让人清淤疏道,甜水再次复出。
一时间,肃州大地的善男信女们纷纷来此乞求神泉甘露,洗身心,去疾病。还真有不少信众喝了这井水把小病给治愈了,信众放鞭炮、送红匾、挂锦旗的热闹场面不时在苦水寺上演。加之果慈还会中医,给人开药方治病,于是被信众称为“大师”,都说他是九华地藏王给肃州派来的大德高僧,是来弘法祈福保佑众生的。
对于复涌甜水,果慈将其归于佛祖的怜爱和师父的功德,就更加不敢慢怠法事操持和修行的精进了。
这天离伏羊节开幕还有两天,夏天的清晨,太阳升起来得早。胡镇长是骑自行车来苦水寺的,他想早点去早点回,免得让人看见一个国家干部去庙里,终是不妥当。胡镇长到庙里有公事也兼着私事。公事是要办伏羊节,镇里研究想让果慈到现场开幕式上站个台,并做个法事,为千头羊做个三皈依,这是噱头,有别于其他地方开幕式的特色。现在办节要吸引人,就要出奇招。过去可以公款请明星,现在明文规定不行了,但规定没有说不可请本乡的和尚。私事是自己这些天忙得内火攻心,牙床发炎,半个脸红肿,打吊水也没有压下去炎症,老婆说去苦水寺讨口井水洗洗就好了,也是无奈之举。伏羊节开幕式还要主持会议,不能半边脸小、半边脸大怪物一样上台出洋相吧。办私事求井水胡镇长有把握,但这公事他还真有点吃不准,听说这年轻和尚谦和,但出家人的规矩多、难弄。他心里没有底,书记说你带上秘书去合适,准中。他无奈,一早就带着镇上秘书骑车像公狗追母狗一样,从镇上奔了过来。
到庙里没见到果慈,小沙弥悟生让他等等,师父在藏经阁读书。
在等果慈时,胡镇长看到驮着小孩进庙门的小呆,不由得想起自己那天被大呆戏弄之事,虎着脸骂了一句:“你那狗熊男人太不像话了,那天把我摆乎狠了,拖个车带个人,能费你多大事哩!”
小呆见镇长变了脸,自觉大呆那天确实不该那样做,便放下女儿风筝,连忙赔笑脸:“您大人不记小人过,大呆为女儿的病闹得心神七零八乱的,俺给你赔不是。”
胡镇长看到小呆那张真诚道歉的胖脸和一直往小呆身后躲的小女孩,就心软了,抬手挥了挥:“算了,算了,这孩子的病可好转些?”
小呆经他一问,低下头,有点哽咽:“跑了不少大医院了,就是治不好,俺镇头小四的妞昨天就死在南京医院,也是这病。镇长,你说俺苦水镇的人得罪了谁?怎么有这病魔害孩子呢?”
胡镇长左脸抽搐一下,火燎燎地痛。“啥人知道是咋回事,你到北京去,我堂弟儿子在协和医院当副院长,你找他治,我这就给他打个电话。”说着就掏出手机,出门打电话去了,嘀嘀答答的声音在小呆听来十分悦耳。小呆对胡镇长就有了另一种看法,其实胡镇长这人还是喜欢帮助人的,记得去年他还组织了全镇人捐助血液病家庭,他一人就捐了一万元。听说,他一个月的工资才三千,老婆知道后气得回县城儿子家住了半年没有回来。他这当干部的也不易,小呆想。
胡镇长进来时肿脸上泛着喜色:“敲定了,你明天就去,包治好。”说着让小呆记下北京医生的号码,“协和医院那是给中央首长治病的地方,准能治好孩子的病。”胡镇长兴奋地说,仿佛他就是包治百病的神医。
“快,谢谢爷,谢谢爷。”小呆拉过来风筝要致谢。
风筝睁着一双失神的大眼睛,盯着那个一边脸大一边脸小的汉子,不敢上前。
“这孩子没出息。”小呆责怪了一句风筝,风筝一摆手跑向了大殿门外,被小呆给追了回来。
走进殿堂的果慈显得十分精神,头发刚剃过,青色的头顶上戒疤红润如珠排列,见到小呆微笑地说:“你来了。”小呆见他的庄严,霎时有些敬畏:“来了,早该来了。”
胡镇长是镇上秘书介绍的,果慈合十道安,把他们引入自己的禅房。
落座定,胡镇长和小呆相互推让。
“镇长公事大,你先来。”
胡镇长想微笑一下,刚扯动笑肌,左脸就如被电击了一下,生疼。“你先给孩子看病,我出去转转,再过来。”说完他先去了苦水井那边。
果慈不拦,只是让小沙弥引路去了。
果慈听完小呆含泪的叙述,才知道这个神情有点蔫的风筝得的是血液病。小女孩今年刚六岁,这年龄是自己丧父丧母的年龄,这罪恶的病怎么能降临在这么幼小的女孩身上呢?自己六岁时虽然不幸失去双亲,但还能存身于世上,她却要离开这个世界了。悲惨!果慈心有所感,起身走到风筝面前,蹲下身来,用手拂了拂风筝的冲天小辫子,望着风筝那双布满忧伤的大眼睛说:“风筝,你在想什么?”
风筝低下头,一会儿又抬起头:“我想上学。”
果慈心中一揪,佛祖呀,请保佑这个小生命,哪怕把我的寿日匀给她。
“你一定会上学的。”
“真的?”风筝仰起头,眼睛里忧伤的雾气在快速消散,露出一束亮光。
“大师说得还有错?给你开服药吃了准好。”小呆在一旁说。
果慈被这句话羞得脸红,他很想说,我不是医生,这病我看不了,那井水也治不了。我只是一个僧人,念经文的僧人,这些经文对治这病是没有用的。但他不能开口,不能熄灭了小女孩求生的念想。
“大师?大师就是能救人命的人吗?”风筝急切地问。
“我不是大师,我也希望自己就是能救人性命的大师啊。”果慈轻叹。
“那我叫你和尚叔叔吧。”风筝歪着头说,没等果慈回答就肯定地喃喃“和尚叔叔”。说完蹦蹦跳跳去院里看水井了。
小呆难得见到风筝这么高兴,心内不由生出喜悦来。
果慈却收敛了笑意,很慎重地对小呆说:“血液病要尽早治,不能耽搁,快到大医院去治。我这里给你开一剂中药方子,只是调剂肝脾平衡的,这病还得去看西医。”说完就铺开纸笔拾起笔墨开起方子来。小呆一直垂手立在那里,拿到药方子如囚徒拿到大赦的诏书,喜出望外,口中念叨:“有救了,俺女儿有救了。”她转身出门,又仿佛想起了什么,折回来,从口袋里掏出一卷钞票塞给果慈。果慈说:“我不是医生,不收费的,你家有病人要花大钱的。”小呆却扔下钱风一般跑出门。
果慈要追她时,胡镇长回来了。
胡镇长心情好起来,刚才用凉凉的甜井水又洗又漱,觉得半边脸疼痛已大减。
“出古怪,这井水一弄,怎么不痛了。”胡镇长笑着落座对果慈说。
果慈轻描淡写地随了一句:“井水不是药。”
胡镇长就忙着把诚邀果慈参加伏羊节去做法事的来意说了,说完还添了句:“这是关系我苦水镇民生的大事,请大师一定拨冗参会,虽说是公事,我们会酌情给费用,你开价,我们给报销。”说完用眼角余光有意无意地瞟了一眼小呆扔在桌上的钱。
果慈没有答应去,也没说不去,只是呷了口茶,岔开话头问道:“胡镇长,贫僧有事想问政府,苦水河已经成了垃圾场,这一河两岸的人都无法生活了,不知政府该何时治理?”
胡镇长如蚕的眉毛抽动一下,也呷了一口茶,微笑道:“大师所言涉及民生,心系百姓的疾苦,敬佩呀!你知道,俺镇无资源无名胜,财政一直只能保吃饭,这几年搞了伏羊节财政税收才有点进项,不过商贩屠夫们只顾生意,不管环境,这羊下水啥的都扔到河里。加之,河上游邻县发展化工业,这污水入河,不就把这河糟蹋成了这番模样,说到治理也非是一个小镇所能为的。”说到这儿,胡镇长分明看到和尚脸上生出不满的神情,就赶忙又说:“不过大师也不要忧虑,我们今年出台铁规,统一管理羊下水,并引进了一家皮革厂,可以加工羊皮,还有肠衣厂也在谈判中,放心,不用两年,这河水俺敢拍胸脯说可以绿起来。”
果慈见胡镇长那张肿脸肌肉抽动,汗珠渗出,暗道:也难为他了。
“先挣个吃饭钱,再来治理,不然没钱咋治?所以,伏羊节要大办,要把天南地北的人给吸引来。你算算,一个人在这儿消费两百元,一天一万人,推算一月三十天,怎么也得赚个六千万,可对?这钱让百姓挣,百姓富了,政府日子不就好过了吗?”胡镇长说到激动处,站起身子,踱起步子来,忘了这是禅房,不是他的办公室。果慈不介意这些,反而喜欢他的率真,佩服他的理政之策。望着大不了自己十岁却老相得像五十岁的镇长,果慈心生怜悯:现在当官不易,乡镇干部更不易。
接下来胡镇长如向县委书记汇报工作一样,侃侃而谈起苦水镇十三五发展规划,让果慈心动且感动起来……
当胡镇长推着自行车走出山门时,已是快到中午时分。山门外,果慈立在白果树下,目送那两位骑车人顶着烈日向镇上奔去。清脆的车铃声传来,让果慈如同听到梵音和塔檐上的风铃声……
五
大红大绿的旗帜,把苦水镇中学操场渲染出一派节日的喜庆氛围。大红地毯铺就的主席台上,一溜排站立着满脸兴奋的嘉宾们,果慈是唯一脸上浮现拘谨不安表情的人,局促使他手脚变得僵硬。
仪式议程很多,胡镇长主持得幽默且庄重。他今天着短袖鸭蛋青色的衬衣,打了个海蓝色领带,头发向后梳了个背头,额头显得饱满硕大,左脸显然消肿了,只是黑眼圈让人感到他有些疲惫。他亢奋地主持着,妙语连珠地即兴发挥,引来台下人潮水般的掌声和笑声。他要是去央视当个主持人一定会红的,果慈心里冒出了这样一个想法。在万众瞩目之下,他盼着仪式早点结束,但领导讲话、商家发言、来宾贺词等等是那样冗长。
果慈端视台下众生,觉得自己如同被耍的猴,他突然后悔来到嘈杂喧哗的地方,使自己的心境有了躁动。他一时不知道自己的目光该放在哪里,是东边还是西边,是前方还是近处,在哪里停驻才合适,最后只得把虚妄打量前方的目光收回,微闭上眼睛,因为,前方是一栋栋高楼。
烈日炎炎,风好像死在来的途中了。站在红地毯上仿佛站在熊熊燃烧的火炉之上,果慈虚汗淋淋,他吞咽着唾液,生怕自己再次中暑倒在台上。就在这时,他听到一声“和尚叔叔”,便张开眼睛去寻,看见那个叫风筝的小妞骑在小呆的肩上,冲着自己呼喊并摇着一面小红旗。大呆作为名厨代表发言时,风筝更是把小手拍得山响,那冲天辫子也如春风吹拂的树苗般摇曳着,那满脸的甜笑让果慈心生欢悦。果慈心念:让孩子兴高采烈应该是大人们心里最慰藉且幸福的事了。大呆发言时,腰也好像直挺起来。果慈见他走过胡镇长身边时满脸谄媚的笑,人呀,真的很容易满足,只要给他荣誉和地位,果慈思忖道。
终于到了果慈为羊群做三皈依法事了。
但见一队队山羊被赶到操场的左侧,白茫茫一片,如果没有咩咩咩的羊叫声,从远处望去,疑似雪地,只不过那雪地在蠕动着。
果慈在众人的目光中,一步一步走向羊群。他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羊赴死,要去往生,他的眉心在跳,人中在跳,心更是剧烈地跳,他能听到那咚咚如鼓响的声音。
一踏入羊群,果慈就如踏入了冰窖,刚才的炎热变成了彻骨的寒冷,他手里握着三支香,竟比三只铁钎还重,他的步履变成沉重且涩滞,他念经文的声音慢慢低去,最后如蚊鸣蚁叫,只有自己能够听到。他还在念经吗?在!果慈知道自己在念,但是让众多看热闹的食客观众生出失望:这大师念的经文怎么听不清楚,这和尚不会念经文,或是哑巴和尚吧?要不是身后随同而来的两位师弟高声诵经,果慈不知道自己如何收场。师弟们也奇怪,在甘露寺诵经最洪亮的果慈今天怎么了?果慈的嗓子亮,在九华山僧侣和信众里有“叫天子”之雅号,他诵经声音高亢,有韵味,声传大殿每个角落,绕梁不绝,今日果慈只是嘴唇颤动,甚是奇怪了。
果慈的嘴唇颤动,心在颤抖,这么多无辜而无瑕的眼睛,这么多长睫毛下闪动如儿童眸子,让果慈不敢对视,仿佛自己是个罪人和杀生者。那些羊儿们咩咩叫着,仿佛在倾诉什么,渴望什么,乞求什么。这么多的生命将要远去,果慈真没勇气去与那些羊儿的眼睛对视,他闭上了眼睛,流下了眼泪。他仿佛听懂了这些羊儿的叫声,充塞耳房的都是:“命命、命命。”果慈在这一声紧似一声、一声高过一声的咩咩声里,一下跌坐在羊群里。他盘腿而坐,合十诵经,突然高声诵道:皈依佛,两足尊,皈依法,离欲尊,皈依僧,众中尊……
师弟们见他破规跌坐羊群,先是不解,后见他又用那“叫天子”的天籁之声诵经,也就跟着他放慢声音。看热闹的观客霎时领略了佛音的圣洁和神圣,纷纷拿出手机照相,有人还直播这条新闻。
胡镇长紧张的脸上露出欢欣的笑容,这就是他需要的效果。他知道那些手机微信一时间就会让苦水镇伏羊节成为万人皆知的热点,这就是噱头。
风筝听到这声音竟然有点莫名的激动。
羊儿们围着这位杏黄色的僧人,慢慢地安静下来,在果慈吟诵的经文中,它们仿佛听懂了一切,是的,我们来这世间的最大贡献就是给人类提供肉和骨。
果慈在羊群中诵经,诵着诵着,突然觉得自己的灵魂出窍而去,领着一丛丛洁白的云朵在飞翔,那白色的云朵就是身旁的羊群。当他再次坠入大地时,经文已念完。但他不想起身,只是想和这些羊多待一会儿。
不知是谁拉住了他的手,果慈睁开眼睛,见到风筝,这个小妞儿,如羊一样怯怯地看着自己。他是被风筝牵着走出羊群的,还是他牵着风筝冲出羊群的,已经不重要了,身后羊儿们不再躁动、不再恸哭,只向着苍天喊:“命、命、命、命。”
白云在上,羊儿在下,僧人心碎,俗众一年一度的杀羊狂欢,开始了。
舞台上演起泗州戏《窦娥冤·六月雪》:天啊天!想我窦娥遭此不白之冤,我死之后,刀过头落血喷白练,三伏降雪,遮满尸前,还要山阳亢旱三年,以此屈冤……
羊儿们知道自己的大限来临,它们的哀鸣传遍苦水镇的每个角落,此时死在路上的风仿佛复活了,把它们的哀鸣和血腥气带向很远很远……
“和尚叔叔你流泪了。”
“羊儿们将死我伤心。”
“你不是给它们念经了吗?”
“可它们还是死了。”
“风筝的病好不了,也会死的,你也给我念个经吧,你念的经真好。”
“风筝——”
街道上,这几句话不知是否被行人们听见,但苦水镇真切地记得有两个人心中下起倾盆大雨,他们悲恸地哭着,哭羊,哭人,哭这苦水镇上的一切。
仪式结束后,两位师弟和小沙弥就找不到果慈了。那天很晚很晚的下半夜,山门被敲响,才见到梦游一般归来的果慈,他没有说话,径直去了禅房,一觉睡了三天,死了一样地沉睡。三天过后,他一切如从前,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上早课、晚课,修禅诵经,只是比过去更忙了。也许忙是一剂药,一剂能使果慈遗忘一切的药,包括杀生。
六
果慈再次到苦水镇是伏羊节快要结束的月末,他是被大呆夫妻俩请来的。缘由是,风筝去北京医院治疗加上吃了果慈的中药后,病情见好,各项指标开始正常。喜出望外的大呆小呆在风筝的央求下,放下生意赶到苦水寺“请和尚叔叔去呆家汤馆一趟”。
果慈听到风筝病情好转的消息,心里就生起欢喜,只是自己一个出家人去他们家做客甚是不便,便答道:“病好了就好,其他就免了吧。”见他推辞,小呆就扑通跪下来,“你是救命恩人,一定要去。”小呆仰着脸,眼里布满焦虑和渴求。大呆在一旁搓着手,好像很冷的样子。
果慈赶忙搀扶起小呆:“好吧,我去。”
其实果慈也想小风筝了。
他们仨是走着去苦水镇的。去苦水镇就得过苦水岗,苦水岗过去是乱坟岗,现在是苦水镇的公墓地。走过那里时,他们变得话少起来,风从岗上来,刮来了死亡的气味,有一家人正在一个很小的坟头上放着鞭炮,还有三两个妇人在呼天抢地哭着。小呆听到哭声就抹眼泪揪鼻涕。大呆大口大口地抽起香烟,加快了步伐,仿佛怕鬼缠身似的。果慈也加快了步子。
转过岗,大呆坐在松树的松根上,招招手对果慈说:“你坐坐。”接着对小呆说:“你先回去蒸馍。”小呆神情低落地走向回镇子那条路上。
果慈打量大呆,这是典型的被朔风雕刻过的淮北汉子的脸,马脸长长,泛黄的瞳仁流淌的是淮北人果敢的光泽,淮河的碱水、面食以及酒气,使这里的男人很剽悍。
“你可抽支烟。”大呆把烟递过来,见果慈摇摇手,就自己叼了起来。
“刚才是镇东的蒋王家孩子殁了,也是那个病,那块坟地上十来个小坟头埋的都是孩子,也就这几年的事。×他娘的,我真不敢打这里走,一走就心焦心寒,回家做噩梦。”大呆大口地抽着烟,大口地吞下去,接着从鼻子里冲出两条小白龙来,“你说这苦水镇还能活人吗?”
果慈不知如何回答,他能说生死皆无常,能说因果报应,还能说生有何欢,死有何惧,可对着那不远的小坟包,他不知道说什么好。“阿弥陀佛”,他只得诵经如此,仿佛皖北大地的一声轻叹。
大呆把烟头一扔,冲着果慈说:“俺们走吧,这里晦气重。”他俩的步子变得沉重起来。
到了呆家羊汤馆,风筝早就迎在那里,一见果慈就跑过来拉他的手,喊着:“和尚叔叔。”
大呆和小呆看到风筝和果慈手拉手的样子,舒心地笑了。大呆好像醒了一样,责骂了一句:“你傻笑个熊,快去整几道素菜给大师吃。”并转脸对果慈大声说:“大师,你可放心了,我这里刚为你买的锅碗盆,一色的新,用菜籽油,不沾半点荤腥,还请了胡镇长来陪你,哈,那狗熊一听你来就忙不迭地答应来。”
果慈被风筝牵着向里屋走,转头告诉大呆:“不要太麻烦为好,我见到风筝就行了,不要什么人陪的。”
大呆抬抬手说:“没事,没事。”
在风筝的房间里,果慈仔细打量这个生病的孩子,风筝果真比过去面色红润了许多,眸子里流出的是黝黑如乌金的色泽,小嘴唇也变得红润起来。“你精神多了。”果慈轻声说道,仿佛默念经文。
“对,对,她好了。”小呆连忙应声。果慈有些诧异,明明是自己心里的话,她怎么听见的啊?
“风筝不会有事。”果慈心虚了一句。
此时,风筝捧来一本厚厚的本子,“和尚叔叔,你看,都是我在病房里画的。”
果慈打开厚本子,一页页慢慢地翻看着,那是一个儿童用心画出的一只只神态各异的羊儿,有黑羊、黄羊、褐羊,更多的是灰白色的羊,其中一只黑耳朵羊,仿佛就是那只曾经舔过自己手心的羊儿。果慈震惊了,不忍再翻看下去,因为,这个小女孩为它们画了一幅幅遗像,人有遗像,羊也有,风筝为它们画了。果慈合上画册,就像要关闭一扇窗户,这扉窗户印满了痛苦和罪恶。
果慈转过脸问风筝:“都是你画的?”
风筝点点头:“在北京病房,我想家就画它,画着画着就不想了。”说完笑了笑。
“对,就是她画的。”小呆在一旁骄傲地证明。
“她很有天赋,长大可以成为大画家的。”果慈垂下眼皮说。
“我只要上学就好。”风筝鼓起腮帮子,说完头就垂下来,那个冲天辫子如矛一样刺向了果慈。果慈心里一紧。
小呆过来要抱风筝,风筝一犟身闪了过去。
果慈觉得有点尴尬,似乎自己说错了什么,他脸红了一下,拉起风筝的手说:“走,我们看羊去。”
风筝听了他的话脸色由白转红自然好看了些,就随着果慈下楼向后院走去。
小呆见他俩走去,伫立在那儿,如院里一棵沉思的树。
走出镇子老远才见麦地,麦地过去是苦水岗的余脉。山坡上,各家汤馆用铁丝网围起属于自己的羊圈,这样一来,就把好端端的山坡搞得七零八落的,远远望去,那山坡上的羊圈如一片片晾晒的尿片似的。
“那是俺家的羊圈。”风筝指着正南方向的羊圈说。果慈抬眼望去,有两个人在羊圈前蹲着叙话。他知道那是大呆和胡镇长,就领着风筝快步向前走去。
在走向山坡时,风筝告诉果慈,羊圈里有头水羊快生小宝宝了,她给那“水羊”起了名叫“宝贝”,宝贝生的娃,就叫大南瓜、二冬瓜、三西瓜、四北瓜……风筝问:“和尚叔叔,你说这些名字可好?”果慈点头。风筝说:“要不叫熊大、熊二、熊三、熊四也行,跟动画片里一样。”果慈还是微笑地点头。风筝停下脚步仰着头对果慈说:“名字起不好命就不好,街上人说我名字不好,命系一线,所以生病了,和尚叔叔你给我改个名字吧。”果慈心里一紧,牵着她的手指一跳,仿佛手指被玻璃划破了。他蹲下身来说:“别听他们胡说,你的名字好呀,飞在天上,俯视大地,多好呀。”风筝听到这句就兴高采烈起来,跳着蹦着向前奔去。
大呆和胡镇长蹲在那里抽烟,他俩的身后地上躺着一只刚杀的羊,四蹄还在抽搐着,一动一动地仿佛要踢开死神的唇吻。
胡镇长和大呆起身要和果慈打招呼。可风筝“哇”地放声大哭起来,冲向大呆骂着:“坏蛋爸爸,坏蛋爸爸。”用脚踢着大呆。
大呆连忙问:“咋了你?咋了你?”
“你把我的宝贝杀了,它快生小宝宝了,我不干,你赔我的羊,赔我的,你个坏蛋,大坏蛋。”风筝继续踢打大呆。
大呆对女儿十分疼爱,从来没有让她这样恼怒过和伤心过,他看了一眼胡镇长。胡镇长满脸不屑,“小丫头,别胡闹,羊是阳间一道菜。”大呆听到胡镇长呵斥女儿心里不悦,但也没有说什么,只是哄孩子:“别哭了,小祖宗,俺明儿个赔。”
果慈脸色酱紫起来,目光里多了愤懑的光,他用手指颤抖地指点着:“你们,你们怎么连怀胎的水羊都杀,你们长了人心吗?”
大呆赶忙说:“现在人都好吃胎羊这一口,今天中午胡镇长说县里来领导,要招待咋弄?”
“是吗?胡镇长,这县领导真要吃胎羊?”果慈倾着身子,怒目圆睁瞪向胡镇长。
胡镇长本能地向后退了两步,嘴角抽出一点笑意:“你看这伏羊节快要结束了,今年全县就数俺镇办得好,县里给了专项奖励二十万,你说这领导来了不得请他们一顿,这吃胎羊是今年才风行的,不得给他们尝尝鲜?”
“你们是什么人呀!”果慈低吼了一声,转脸对大呆说,“你们估个价,这羊我买了,我要把它安葬,你给个价吧。”说完走到羊前,用颤抖的双手拂过那只羊的脸颊、羊角、羊颈,刚到那隆起的羊腹部时,便放声大哭起来,哭声如牛哞,传得很远很远……
胡镇长向大呆嘟囔一句什么,大呆为难地说:“这胎羊不卖了,冲着风筝我也不能卖了。”胡镇长用不解的眼神打量他们仨,又紧盯着大呆,大呆坚定地说:“不卖。”胡镇长用手抹了一下满脸的汗,“不卖算■,我另找人家去。”说完悻悻走下山去。
正午烈日当空,苦水镇上的人们本该躲到荫凉处去乘凉,但这天没有,许多人跑到山冈上看一位僧人为一只水羊下葬,甚是奇怪。谁都不知道那位僧人在羊坟前发了愿,要拯救所有的胎羊。
孤松,羊坟。
一位僧人诵经,一个女孩在哭泣……
七
苦水镇上的人再见到果慈时,是葬羊的第二天上午。他带着一个小沙弥从街头第一家汤馆开始下跪求水羊。他跪在汤馆门前诵经,小沙弥打着一个白布幌子,幌子上有“发慈悲,救水羊”六个大字,那字墨迹未干,一看就是刚写上去的。那个场面引来了众多食客的好奇。店主们走出来,问和尚这是干啥子?果慈只说如果有水羊就卖给我,或送给我;我待小羊出生断奶后再还你,只要你别杀水羊就好。有店家爽快地答应以水羊相送,也有少数不肯答应。
风筝听小呆说和尚叔叔在街上跪求水羊,就一溜烟跑出门,在大街上寻找起果慈来。
这是伏羊节的最后一天,人们来得更多,蜂拥而至,仿佛不在这天吃上一口羊肉喝上一口羊汤,下辈子都吃不上了。在这稠密的人群里,果慈是人们驻足观看的一个大景点,比节日里跑旱船还要热闹。
风筝总是跟在果慈的身边,给他送水喝,为他扇扇子。
果慈说:“风筝听话回家去,这天热,别中暑了。”
风筝摇摇头,不语,就是跟着他走。
一店一跪,慢慢地,果慈身后多了不少下跪求羊的善男信女。
当收到第十只水羊后,果慈就不知如何坚持下去了,他带来的钱已经告罄,没钱收羊了。那些善男信女们听小沙弥说没钱收羊了,就纷纷解囊相助,风筝也一溜烟地跑回家找大呆小呆去要钱。
在捐钱的人群中,果慈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那个微胖身躯的胡镇长向小沙弥的布袋里扔了一沓钱就转身挤入人群中,一晃就不见了。果慈看得真切,炙热的心里升起一丝清凉。其实,胡镇长对果慈的跪求水羊,一开始就有点放松警惕,他以为这也是炒热苦水镇伏羊节的一个热点,他让秘书注意网上的反应,果然点击率一下上升到一百万了,因而他也就来捐了钱。
风筝牵着大呆和小呆一起来的,小呆说:“俺们捐一个羊头的。”说完就把一沓钱扔进了布袋。
果慈看了他们一眼,合十。
苦水镇上的人是善的,果慈心中想着。
有善人,也有恶人。
大毛汤馆店门口,捆着一只水羊,大毛口里叼着一柄刀,向羊走去,他刚抽过一管白粉,有些兴奋,哼着小调走着,仿佛腾云驾雾一般,他的两个儿子也刚抽过白粉,傻笑着跟在大毛身后。
羊早吓得跪了下来。
大毛用大手把水羊的头按着,右手举刀准备白刀入羊颈、红刀带血出时,就听到一声断喝:“施主!刀下留命!”果慈的喝声竟有金石之气,把大毛吓得一抖,刀都失手掉在地上。
“你瞎咋呼啥?你个小和尚。”大毛回过头看着果慈。
果慈把来意一说,大毛来了兴趣,他直起腰来,斜了一眼果慈,“我要是不卖给你,决心要杀呢,你怎么办?”
果慈说:“我没办法,我只得跪求了。”说完就跪在店门前。
“真犟,你跪,我看你能跪多长时间。”大毛嘿嘿怪笑了一声就回汤馆了,留下果慈和一众善男信女。
大毛以为一个和尚大热天不能跪多久,没想到果慈一直跪着。大毛骑虎难下了,再者,店门前这么多人看着这西洋景,没有人进馆吃汤,生意明显受影响了。他心里恨起和尚来。
果慈这一跪就是四个钟头,已到了太阳急着下山的时辰。
屋外的街面上,已经簇拥起众多的食客。微博和微信让跪求水羊的事件持续发酵,已经变成了公众话题在网上热炒。话题从“慈善和尚救水羊”“我们该不该吃水羊”“吃水羊后面的人性考量”,到“苦水镇的伏羊节的罪恶”“刘大毛其人”“刘大毛的矿难人之死到水羊之殇”,掀起了一层层波澜。
苦水镇的书记在省委党校学习,听到这消息立刻打电话让胡镇长及时处理此事。县委书记也让县委宣传部传达指示,马上消弭事件影响。胡镇长这时才认识到事件的严重性,他赶忙跑到大毛羊汤店,对果慈说:“大师,这羊的事就到此为止吧。”
果慈摇摇头,无语,目光坚定地望着店门。
胡镇长眉头一皱“嗨”了一声,一拍大腿进屋想去劝大毛,只见大呆正跟在大毛屁股后劝说着:“大毛,你就把那水羊卖给他吧,你看人家和尚也怪可怜的。”
胡镇长赶忙跟着劝说:“算了就卖了吧。”
大毛犟劲上来了,执拗着不同意,越劝越不同意。
大毛的大儿子说:“这和尚不走,今晚生意得黄,大锅里汤都熬干了,也没卖出去一碗,还把老子在网上弄成了反面人物。”
“奶奶的,把他赶走。”大毛趿着拖鞋,觍着大肚子走出去,冲着果慈喊道:“小秃驴,你在这里跪半天了,不累?”
果慈摇摇头:“不累。”他说的是真话,他跪的地方刚好和那只捆着的羊目光相对,在羊的深情目光中,他忘记了一切。
“娘的,你给老子躲开,不走,我可要泼汤了。”说着,大毛就端起了那锅热汤,“滚蛋,滚蛋,俺这不是庙门。”
果慈不动,众人睁大了眼睛,空气霎时凝固了。
大毛脸上挂不住,他分明看到众多人的眼睛在看着自己,分明是一种讥笑的目光。这时,他的二儿子递上手机,“爹,你看你上节目了!”大毛一斜眼,看到手机里自己端锅的丑样儿,一时气就上来了,他大喊了一声:“老子泼汤了。”说完真的把锅里的汤泼了过来。
风筝见汤泼过来,“哇”的一声大叫冲到果慈身前,果慈挺身将袈裟向下一摆,把风筝罩在身下,那锅热汤泼在果慈手臂上,千条蛇咬一样疼。果慈强忍着痛低头看看风筝,见她没有烫伤,冲上前推了一把大毛子,骂道:“混账!”
大毛被推倒在台阶上,头磕出血来,爬起来,一挥手指挥俩儿子:“给我打!”两个儿子便举着木棒和铁铲向果慈打来。
“住手!”大呆顺手拎着杀羊刀冲过去,“谁伤风筝老子就杀了他。”
果慈被两个山豹一样的汉子打倒在地,满脸是血。风筝趴在果慈身上大哭,小呆跑过来护着风筝。大毛的两个儿子还是拼命打着果慈。
果慈一挺身站起来,一把夺过大呆手里的杀羊刀,朝两个汉子冲过去。
“毁了,和尚你别杀人!”胡镇长冲了过去。
只听一声“啊哟”,小镇一下归于寂静。
“我的儿,我的儿,我要烧了你的庙,杀了你的人。”这是大毛的声音。
…………
僧人果慈被公安逮捕了。果慈持刀伤了大毛家的二儿子,也伤了胡镇长。
大呆、小呆真的呆了,傻子一样立在那里。大呆想自己不该拎着刀过去,不拎刀,果慈就不会抢刀伤人,所以,自己是罪人。他跟公安说刀是我拿的,人是我伤的。大毛骂他:“你逞什么鸟能?”警察严肃道:“你回去,没你的事。”
警车上,全身颤抖的果慈在脑中拼命想理清刚才发生的一切,他不知道自己为何会这样,他对自己喊:我是一个护生的,救生的,怎么会杀生了?罪孽啊,罪孽啊!
他闭上了眼睛。
八
苦水镇的人咂摸咂摸这事就有点不是味了,就三三两两来到大呆羊汤馆,说长说短,千言万语归了一句话:我们该救果慈和尚。众人推来推去,最后推选了大呆、小呆到县城公安局去求情,说去城里的开销大伙分摊,要把果慈捞出来,我们苦水镇的人要仁义。
小呆说俺家风筝咋办呢,街坊说俺们轮流带着。
风筝说:“娘,我不用你管,你放心去吧。”说完从屋里捧出那本画册说,“把这给和尚叔叔带去,他就不怕了。”她的话引得汤馆里唏嘘一片。
大呆、小呆和小沙弥悟生三人终于找到了公安局,却进不了大门,被门卫挡住了,正在束手无策时,却见胡镇长哭丧着脸走出来。他吊着打绷带的胳膊,跟《红灯记》里王连举一样,一见他们仨就虎着脸问:“你们来这儿干啥?”
大呆觍着脸说:“俺想让公安放了果慈。”
胡镇长不耐烦地冲了他一句:“这是公安局,不是你家羊圈,你想开就开,想放就放?”
大呆不吱声,低下头。
“走,跟俺回去。”胡镇长口气缓了下来。
“俺不走,见不到果慈,俺不走。”小呆拉了拉大呆衣角嘟哝了一句。
胡镇长没理他们仨,朝自己的车走去,走近车门转头说:“我也是来为他求情的,我和大毛儿子都是轻伤,赔点钱就可以出来的。那狗日的和尚,非得在看守所里不出来,说要赎罪,你见过这么傻的人吗?傻鸟一个!”说完拉开车门,哐地把车门一关,冲着司机喊:“开车,回镇。”
大呆、小呆、悟生傻了一样望着胡镇长的车远去。
大呆心里说,这胡镇长也真的还有仁义。
小呆说:“果慈在看守所,俺们就去看看他吧。”
…………
他们仨终于在看守所见到了果慈。
果慈双手敷着烫伤药膏,他神情黯然,眼圈发黑,面色发青,嘴唇干涩——他已经五天没有睡觉了。
“你们不该来这里,这是罪人、犯人住的地方,你们走吧。”果慈低下头说。
大呆结结巴巴道:“这事怪我,我不该操刀。”
“与你何干,是我的罪孽啊!”果慈鼻头一酸。
小呆哽咽着流着泪。
“你们走吧,我要回监狱了。”果慈站起身。
小呆大声哭起来:“风筝想你,她要我把这个带给你。”
果慈听到这句话转过身,抬起头,看向小呆。小呆把那本画册送了过去,果慈接过,双手送给警察,对小呆说:“你回去告诉风筝,我会看的,让她好好养病。”接着看向悟生:“悟生,你一定要把求来的水羊养好。”
悟生点头说:“师父你放心。”
果慈微微一笑,就立刻收回笑容,转身走去,留下来的是一个被灰色僧衣裹着的瘦削背影。
后来的日子,果慈每夜关灯前总要打开那本画册看上一遍,看看风筝画的羊,想想苦水镇,想想风筝那个可爱的小女孩,耳畔就会响起羊儿的“咩咩”叫,就会听到那个童谣传来:小羊小,吃青草,吃了青草长羊毛……那首童谣是风筝教他唱的,那时他跪在大毛店门前,风筝问他跪着累不累、膝盖痛不痛。他摇摇头。风筝又说:“你要是累了,我教你一首儿歌吧……小羊小,吃青草,吃了青草长羊毛……”但他还没来得及学,事情就发生了。每天晚上,果慈只有把画册压在枕头下才能睡去,他会在梦中放牧着一群咩咩叫的羊群,梦见自己唱着童谣,在羊群里慢慢行走,远处,风筝笑着,奔跑着,银铃般的声音四起——那是他最惬意的时候了。
胡镇长回镇后,组织人力物力收购水羊,发布了在苦水镇禁止杀水羊吃胎羊的公告,之后在一张白纸上写下了辞职报告。
秋日的一天,果慈出狱了,他没有回苦水寺,一路向南化缘回到皖南那座佛山圣地。苦水镇人不知道他的行踪,只当他还在狱里呢。
九
如约而至的雪,把皖北大地变成白首白须的老者,呵着白气蹒跚地走进年关。
苦水岗的白雪已是半尺厚,松树被雪压得低下了头,如果不是坟地上有哭声和爆竹声,这里真是寂静。
大呆在坟地上直不起腰,佝偻着。
小呆如一座麦垛瘫坐在那里号啕着。
他们面前的小坟,也覆盖着积雪,那是七天前刚刚垒起的,是风筝的坟墓,是苦水镇得白血病殁了的第三十二个娃娃坟茔。
“我日你娘,我日你死娘,你夺了我娃的命。”小呆在诅咒病魔。
大呆不知说啥好,只是不停地揪着鼻涕,向不远处扔去,这动作过去是属于小呆的。
离小坟群不远处,传来鞭炮声,那里刚葬完大毛。大毛三天前死于狂犬病,他是被流浪狗咬了一口后发病的。那天大毛找不到白粉,见谁都烦,就踢起那只伏羊节过后一直蜷在墙角的流浪狗,那只貌似老实可怜的流浪狗,竟然一跃而起咬了他一口。他虽然把狗杀了,却中了狂犬病。
炮声响过,大毛的两个儿子磕完头,就领着一群人有说有笑地向镇上走去。走到小坟群时,他们看到大呆、小呆在烧头七纸,就哑了声,不由得围了过去。
已经卸任的胡镇长走到大呆面前,拍了拍大呆的肩头,叹口气陪着他把纸钱烧完。众人想把小呆从雪地里扶起来,可小呆怎么也不愿意起来,脚乱蹬,口里大骂着,泼妇一般。
胡镇长说:“你们别扶她,由她去吧,她心里难受。”
众人听到这话就停下了,虽然胡镇长已经不是镇长了,只是镇民政科的一个科员,但他的话在这里却管事得很。
小呆趴在雪地里哭着,如一只巨龟。
大呆向众人挥了挥手,“快下雪了,你们先回吧。”
胡镇长又叹口气,低垂着头离开坟地,众人也随他走了,一股黑色的人流在雪地上,缓缓地向苦水镇流去。
小呆趴在雪地里哭着,大呆慢慢退下手里那串佛珠,悄然扔进焚烧的纸钱堆里。霎时间,一缕异香升起,小呆惊诧地望着大呆背后的地方,那里应该是苦水寺。大呆不解地转过头,也向苦水寺的方向眺去。
远处,只有一片空茫茫的雪幕。苦水寺早在一个没有星光的深夜被烧毁了,当时火光冲天,烧了三个小时,把那里的一切变为废墟——有传言说那是大毛派人干的。
“你看啥呢?”大呆望着发癔症一般的小呆,有点害怕。
“你听……”小呆侧起左脸来。
“听啥呢?”大呆没有听到什么,只听见几声乌鸦的怪叫和积雪从松枝上落下的声音。
“小羊小,吃青草,吃了青草长羊毛……”小呆哼唱起来。
大呆眯着眼再次望向苦水寺的方向。雪原之上,先是一个黑点,由一个黑点变为两个、三个,接着是一条长线。
“咩咩,咩咩”,寒风里分明传来了一阵羊叫的声音,一声紧似一声,越来越响。
下雪了,从天而降的大雪,如羊群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