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2-11-28 来源:安徽作家网 作者:安徽作家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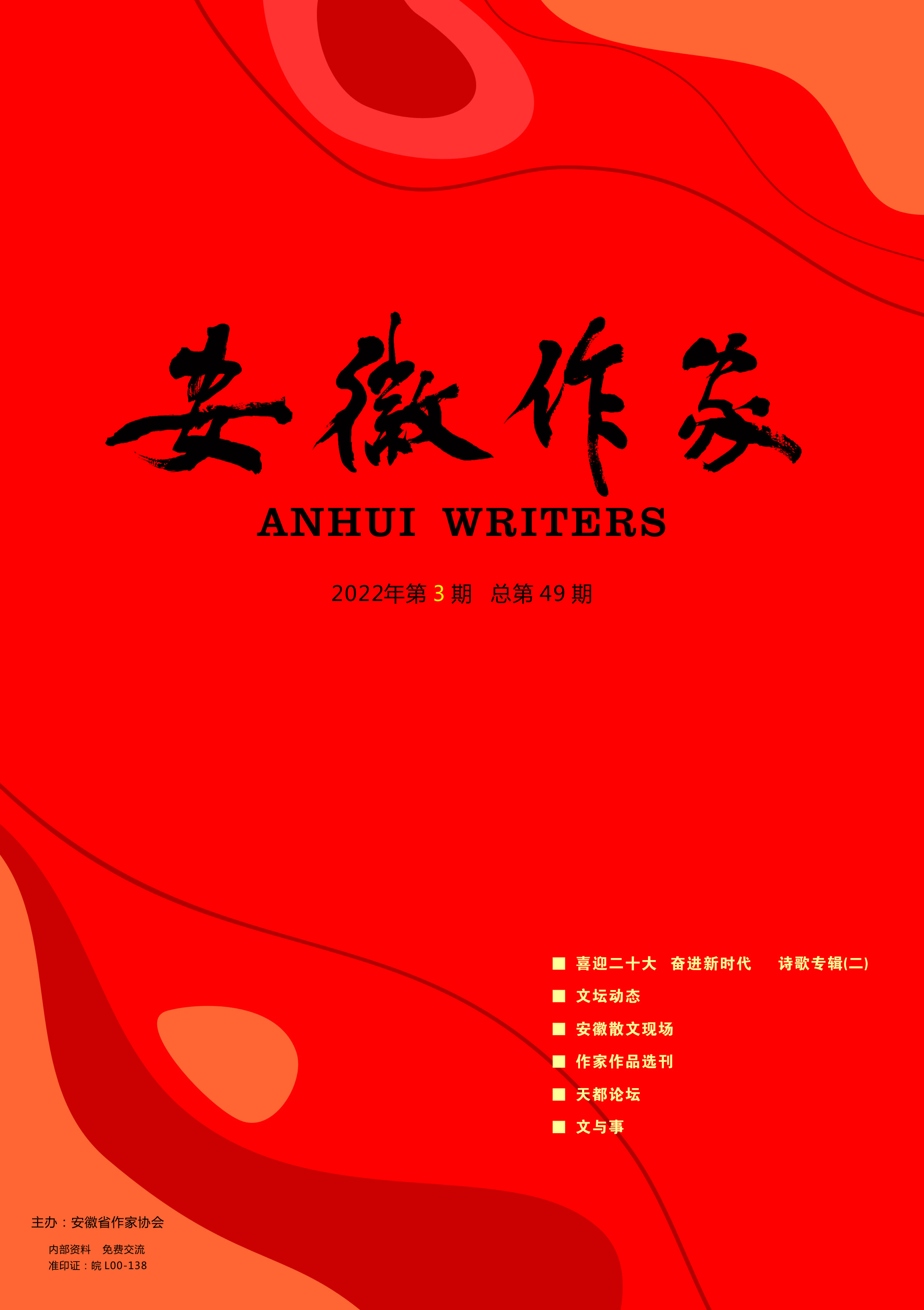
作品欣赏
散文观:文学作品要给读者带去精神上的思考,并体验到愉悦,这愉悦当然应该是美的。不能给读者带来思考以及美的享受的文字,不能称之为文学作品,散文当然不能例外。
扶贫记
金国泉
我突然感到我去扶贫的村寨,那个地处泊湖边的团山村民风少见的纯朴。在这样一个泥沙俱下、雾霾里看鲜花的时代,它悄立湖边,既低头也仰望,甚至远不止于纯朴,而应该是醇朴,淳厚、醇香间挟带着质朴,一种能让我品着甜、含着饴、尝着香的味道,这味道似乎到现在还在我唇齿间激情地荡漾着,一种美到心尖的感觉。
我的家乡望江县是国家深度贫困县,在今年脱贫摘帽之列。也就是说几十年来我生活、工作一直都在本土,像许多人一样没有真正离开过家乡,一直没断过奶,靠家乡的山水滋养着,依家乡的丘陵山冈起伏着。对,家乡的确到处是丘陵山冈、湖汊塘堰,有顺口溜为证:“黄土冈,丈把高,大水淹来就齐腰。湖里游,沟里滚,日晒三天成火坑。”怕涝、怕旱是家乡一块厚厚的胎记,真的摸不得,一摸必生痛,真的经不住敲打,一敲打必伤经痛骨。
我曾在散文《泊湖记》中这样描述过,泊湖横跨皖鄂两省,从安徽望江华阳镇进入长江,应该是长江在此长期形成的一节“盲肠”。现在看来并非如此,泊湖应该是长江这根脐带上拴着的一个孩子,由长江滋养着、灌溉着,两千年仍然未断。实际上,人类生存的过程就是挣断脐带的过程。
春节前夕县里安排了一系列活动,扶贫队长老胡告诉我,春节前每位帮扶人必须走访慰问其帮扶对象户,了解他们春节期间的生产生活,送去关怀温暖、祝贺祝愿。收到这条消息时我在外地挂职,但那不是能例外的理由,老胡嘱咐了我。实际上,涉及到扶贫的事,几乎没有理由例外──我感到,在深度贫困县里,每个体制内的人都具有这样一个身份,这样一分责任,甚至也不仅是体制内,它@所有人所有单位,我等全部被装进了这个箩筐中。
今天是星期天,我早早就起来了,与我的对象户通了电话,妻子问我为什么那么高兴,我回答不上来,但我知道在这方面我比我的那些对象户还要容易满足。因为他们平时都在外务工,一年之中几乎不回来。连面都见不到怎么帮扶?这个责任实际让我们这些帮扶人感到莫名的大。
仅仅打个电话是帮扶吗?双方经常都在这样责问与追问。
特别是汪华中,往年要到腊月二十七、八才回到村子,而正月我们还没正式上班他就奔回到了他的打工地。我常常与他开玩笑,你这几乎是不给我与你见面的机会呀!
我看了一下日历,今天是腊月二十二,他居然在家,与我通话的语气居然不像往时那样硬邦邦,而是露出了平时少有的绵柔感。我怎能不高兴!他常年一个人生活并生存着,父母早年不在了,一个哥哥已成家立业不在一起生活。三十出头,人相当老实,腰板相当结实,但性格也相当结实,结实到有些刚硬,可能正因为如此,至今他仍然长年在乡村与城市之间徘徊着,找寻着,既无牵无挂,也有牵有挂。我常常想,三十出头的小伙子,上不用养老,下不用养小,咋成了贫困户?有一次我曾壮着胆问过他,他说他就是贫困户,不行吗?我没话说了,他理直气壮,我当然就理不直、气不壮。与他类似的我的帮扶对象户还有一户,只不过年龄小一些,比我儿子还要小,原来属五保对象,这样的情况属贫困户就不用壮着胆子问了。他从小父亲病重,欠下一笔债走了,母亲改嫁他乡,留下他一人。两间破败的瓦房在我还不认识他时就已经坍塌了,屋基上长满了野草,夏末时,比人还高。在乡村,特别在贫困的乡村,没人的地方总是会长出这样大片大片的野草,长得让人心慌意乱,大约是这个原因,古人干脆就叫它荒草。好在他母亲改嫁的地方并不远,他不用去管这些荒草是怎样强行霸占他的屋基的。他曾告诉我,叔叔待他也很好,每年打工回来都在叔叔家过春节,这也让我感到他的家仍然在。
在贫困的农村出生并长大,我对贫困当然熟悉到有自己许多不变的标准。有些标准是让我生痛的,从内心里生出来的痛,就像我的帮扶对象,他们那深一脚浅一脚的身影,总是那么沉重,总是让我想起罗中立的油画《父亲》,那时时锁着的愁眉像他们的步子一样展不开。是承载的太多还是乡村的水泥路太窄?但乡村实际是天开地阔的,是能跑大车小车的,每一辆都必须经过乡村的,在乡村掉头在乡村拐弯,田野里无论是冬季的麦浪,还是夏季的稻禾,都是那样的籁籁洒洒,每每都是朴素与亲和,心会旷远,耳会清爽,眼会澄明,甚至就像眼前道路两旁已然枯萎下去的狗尾巴草,在这个冬日的暖阳中仍能让我感到丝丝白洁的暖流,如果我们将它拔出来,它的根必定是鲜活脆嫩的,谁都会忍不住对着它深深吸一口,那充满生命的泥香。
记得上次来时,道路两旁还是满田野满山冈的金黄,现在如释重负了,远远望去只剩黑黄的稻茬,一堆一堆的草垛错落在田埂上,有牛犊缓步,有鸡鸣狗欢,有三五棵灌木青绿在薄薄的冰凌中,给人一种舒畅的感觉。老胡把车停在路边说你一个农村长大的孩子咋那么矫情?我又回答不上来。是矫情吗?是,也不是。这个村子虽与我老家无本质上的区别,但也有隔河隔岸的不同,“三里不同言,五里不同天”。我虽不与它朝夕相处,但来去之间,鞋帮上免不了粘上了它的泥土,手掌上免不了粘了些它青涩的草香,心自然就有了某种牵挂与期许,人与人,人与村庄……概莫能外,华中、护斌、艳伢……每一个名字都有了岁月的厚重与纯净,即便我们不牵着挂着,他们也仍然在他们自己的那个星座上24小时地奔腾,365日地打磨,唇红齿白,笑盈盈的。
我先是到了护斌叔家,老两口都已八十临近,没有儿女,他曾告诉我,早年抱养过一个女孩,又乖巧又漂亮,刚满十八岁那年打农药,不幸中毒夭折。每谈至此,二老脸上短暂的兴奋便转为很沉的漠然,是悲苦二字无法形容的。时间让他们白发丛生,时间对痛苦的打磨,裂痕虽除,但磨损度非常大,像磨刀石比原来低矮了许多,自此老两口相依相靠,没再起任何波澜。他自己右腿早已经行动不便了,到田间地头劳作都要靠电瓶车送他一程,妻子肺部、腰部都做过手术。村里为他俩办了低保,领了慢性病证。就是这样一对老夫妻,我每次到他家,他都是笑呵呵相迎,那种对生活的坦然与承接的确让我心生敬重,敬重中有道不明的心酸。
他养了两头牛、三十只鸡,还种了两亩玉米,获补贴3000元,菜园里有菜,银行里下半年的低保补贴还没取呢!他像数家珍,我也像听新闻,但这新闻有盐有油有柴火,就是一道上好的土菜。就像刚进他家门时看见他提着的篮里的那几颗白菜,清淡可人。我注意到,他用的仍是上个世纪流行的菜篮子,而非塑料袋,这道风景在我的家乡仍然普遍着。村民们制造的垃圾,他们自己基本能处理60%,比如厨余的东西可以喂畜禽,比如果皮、果壳直接就是有机肥,那剩下的40%除化肥、农药,几乎就是城里人带过去的,或过度包装,或尿不湿塑料瓶……
我掰着指头算垃圾账,他却指着篮子里的白菜说,经过霜冻的白菜好吃,又香又脆。这些永远被我们俯视,匍匐在大地上的白菜,我们实际需要弯下腰去才可采摘。它无论经过多少风霜雨雪,总是一脸青翠地面对,一心白洁地生长。且霜打一次,其味就香脆一分。
我家园里的菜自己吃,不下肥,不打药。今天中午就在我家吃白菜烧肉吧!没在我家吃过一餐饭,过年了,也该吃一餐。你放心,肉也称回来了,鸡也顺了,鸭也顺了,就在那──我的家乡,过年用的东西都不叫杀,叫顺,图个吉利──他用手指着吊在那里的一大串猪肉,足足有一二十斤。我叫村里干部来陪你,我家也不是那样脏呀!我知道老人在用激将法,他比那颗白菜还要善良与洁净。记得有一回,我看见他家茶几上有因农忙而没来得及擦去的尘灰,便拿起抹布想帮着擦一擦,老人一下子激动得不行,连连说那不得了,要午雷轰顶了,他把自己压得那么低,把我们这些所谓城里人看得比什么都贵重。
我说不是那意思,护斌叔,我从小就在地沟里爬,田沟里滚,我们家也是吃泊湖里的水,你家到我家只隔两个湖汊,很近。说脏,我们一样脏,说干净,您老比我们干净多了。主要我今天必须见一下汪华中,约好了。
那你去吧。见我如此,老人不再坚持。他告诉我华中在家,刚才去园里摘白菜回来时看见了他。华中这孩子有喜事了,你知道不?我说我不知道,什么喜事呀?他要结婚了。这真是天大的喜事,难怪今天早上讲话语气不一样。
从护斌叔家出来,刚走上村中正路,远远就看见华中站在门口喊金哥。一声金哥朴素而真诚,就像他家刚贴上去的大红双喜字,喜洋洋的。没有了上次见面时胡乱穿着的邋遢,岁月围困的沧桑此时被他一身崭新的西服赶走了。
金哥,真的感谢你,帮我拿到了修房子的钱,你看我这房装得怎么样?华中说的是危房改造资金,他家符合这个条件。我说是村里乡里帮你把资金申请到位的,我真的没帮什么忙。趁着华中为我倒水,我注意了一下他家装修一新的三间平房。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房子也爽着,那些家具也爽着,那曾经漏过雨水的地方,现在严丝合缝,只透喜气,泪痕一样的污迹没有了,媳妇在灶间忙碌着,真是有女人忙碌的地方就有男人安稳的家。他说他与媳妇是去年在一个厂子打工认识的,准备正月初六办个喜酒,到时你一定来喝一杯,要像帮我扶贫一样帮我撑个面子。
这顿酒我一定来喝,你不请我也要来。我问他去年挣了多少钱。他笑着说反正我办喜事不用错钱,“耍滑头”中张开着憨厚。他又甜甜地喊着他媳妇,我没听清,但我听到了他叫媳妇把准备好的东西拿给我。
金哥,这是我俩的一点心意,你一定得收下。我一看是两条中华烟和两瓶酒,一下站了起来,你这是什么意思?是要打我的脸呀!他俩也激动起来,一个拉,一个拽。我说那个危房改造是你应该得的,就连乡里村里也不用感谢,更何况我!我边说边挣脱边往外跑,见我跑出了门,华中居然追了出来,我马上严肃起来,华中,我告诉你,你再跟着我,我翻脸了,永远不理你。见我一脸没见过的认真,他愣住了。快回去,媳妇在等你烧饭,初六我来喝喜酒。
车子发动后,我看见华中仍然愣在那里,一动不动,不知是前进还是转身,冬日的阳光下,一脸无助的茫然,憨憨的像做错了事的孩子,他手中装着中华烟的红方便袋,一晃一闪,有暖意,有无邪的深情。
在回来的路上,扶贫队长老胡说,两条中华烟和两瓶酒,可能要他们半年的积攒呀!这些村民仍然奉行的是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我知道我甚至没给他滴水之恩,是他们自己一步一步艰难地前行,一锹土一锹土去培植,一锄头一锄头去挖掘,他们的温情善良就如村庄旁的溪流慢慢渗透进了这一锹一锹挖着的贫瘠的土地里,这些丘陵山冈因这良善温厚的灌溉而麦子抽穗,稻花飘香。
(选自《安徽作家》,2022年第三期)
作者简介

金国泉,男,安徽望江县屠家田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安庆市评论家协会副主席。诗歌、散文、文艺理论散见于《诗刊》《文艺报》《星星》《天津文学》《散文》《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山东文学》《诗歌月刊》《青海湖》等报刊。曾获吴伯箫散文奖及安庆市文艺奖一等奖。著有诗集《记忆:撒落的麦粒》《我的耳朵是我的一个漏洞》《金国泉诗选》及散文集《大地苍茫》等多部。
作品欣赏
散文观:当我翻开一本散文集,就是想进入作者的内心场域,通过阅读感受作者藉由语言、思想、性情,传达的生命观。我面对的不止是一本书,而是一个有灵魂且有温度的人。阅读,就是和这个人隔着时空相见、交谈。希望自己的书写也有这样的品质。
在河边相遇
项丽敏
蝉歌人间
立秋后的第二天,台风降临。
台风携来风和暴雨,一场交战之后,盛夏在满地落叶里离开季节的门槛。
这是我生命中第四十七个夏天。我不知道这个数字是长是短。相比只能拥有一个夏天的蝉,这当然是长的,而相比山中能活上几百年的树,这又是短的。
我的祖母和外婆在人间活了五十九个夏天。小时候觉得这个数字太短了,让我隐隐恐惧,仿佛一道阴影横亘在那里。现在看来,其实也不算短。以她们早已破败的肉身和沉船样的生活衡量,五十九已是极限的数字,无法再承载更多了。
我的母亲也曾经恐惧过,在五十九岁之前。她焦虑,沮丧,脆弱不堪,觉得自己很难突破这个数字。而这之后,母亲渐渐放松了对时间的警惕。不知道母亲是否有这样的感觉:在跨过了五十九这道魔咒般的门槛后,每一天的到来都是余生,是上天加赠给生命的假期。
如果母亲能有这样的感觉,她就会比较容易获得幸福。至于我,很早就有这样的感觉和认知了,早到已不能准确说出究竟是哪一年。
三十岁,我在日记上写下加缪的一句话,“在隆冬,我终于知道,在我身上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
隆冬就是死亡的威胁,而夏天就是复活的力量。
人的一生应当不止一次出生,也不止一次死亡。第一次的死亡来得越早,再生就会来的早一点。这再生的生命将属于你自己,你将像蝉的若虫一样,在蜕变后,拥有与之前完全不同的生命。
不是每一种死亡都能顺利的摆脱旧躯壳,复活,再生。再生需要能量,也需要运气。
曾在记录片中看到蝉蛹蜕变的过程——若虫从泥土下爬出,缓慢地爬上一棵树,抓紧树皮,背部的壳渐渐裂开一道缝隙,脑袋从缝隙中挣出,接着是三对细足。幼蝉的上半身悬空着,奋力将躯体向后仰、仰,仰成倒挂的角度,让尾部从壳中挣脱出来。
一些蝉的若虫羽化成功了,挣脱了壳的束缚,吸收阳光的热能,让翅膀迅速生长,变得坚实有力,可以带它飞翔。而有些若虫,刚从泥土下爬出就被蚂蚁围攻,成为蚁群的食物。
看到蚂群排着队,涌向蝉的若虫,我的身体也有一种被咬噬的痛感。我无法憎恨蚂蚁,这是自然法则的安排。我只是为若虫悲哀,在泥土下幽闭了那么久,从没见过阳光,没有发出过声音,就永远失去了原本可以拥有的、能够热烈鸣唱的夏季。
整理《山中岁时》的书稿时,发现自己多次书写到蝉。诗歌里也是——偶尔翻开新出版的诗集,隐居其间的蝉歌就溢出来。
为什么会这么频繁的写到蝉,难道在我的生活里就没有别的声音?只有蝉歌,这单一又不知疲倦的声音贯穿始终?
是我的听觉对蝉歌比较敏感吧,总是能在漂浮空气的声音里捕捉到。当你敏感于什么的时候,你就能在纷纭的事物中感知到它,看见和听见它。而当你失去这种敏感时,即便身在其间也惘然无知。
对蝉歌比较敏感的原因在于,我一直就居住在大自然的事物之中。蝉是我无法忽视的近邻,看不见它,但我知道它就在那里。在我已经历的四十多个夏天,多数时候,只有蝉唱陪伴着我,从清晨到黄昏,用它银亮、宽阔又寂静的歌声充满着我。
夏天离开了,但夏天并没有走远。它还会回来,在台风退下之后。
没有一种离别是那么轻易的,斩钉截铁的。每一种离别都要经历再三的犹豫,牵扯和徘徊。
而秋天的到来也不是在夏天离去之后。秋天早就来了。在夏天的宴席最热烈时,秋天就装扮成一丛百日菊,一只红蜻蜓,一树马褂木的黄叶子,还有蟋蟀弹奏的小夜曲,悄然到来。
秋天潜伏在盛夏众多的事物之中,也潜伏在一个看起来很强壮的人的身体里,在他不在意的时候,袭击他,让他在一夜之间疼痛,衰老。
秋天是盛夏的密探,也是盛夏的叛徒。但秋天也眷恋着夏天,模仿着夏天。
蝉的吟唱就是秋天眷恋夏天的证据。无处不在的蝉歌,并没有因为夏天的离去而消失,它的韵律更为婉转、丰富、从容,从单声部变成多声部,反复循环的安魂曲。
一个人走在林荫小道,听着蝉歌,觉得这就是永恒了。
虽然有点孤寂,我还是喜欢这样的夏天——除了蝉歌,听不见别的声音,也听不到自己的声音。
然而我似乎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本领,能在蝉歌里听到万物之声。
这万物也包括我。
有蝉歌就够了,不需要更多了。如果余生还有很多个夏天,我希望仍旧这样度过,仿佛永远过不完暑假的学生。我会继续将听见的蝉歌录下来,以散文和诗去保留,以人间的文字去收藏。
在河边相遇
有好多天没听到蝉鸣了。进入九月后接连落雨,虫声稀疏起来,蝉鸣也像被一只手抽走,消失于四野。
蝉鸣就是漫长夏日的烟花,当烟花燃尽时,安静下来的世界似乎也失去了一种光芒。
耗尽燃料的蝉从树枝纷纷落下。不过仍有一种蝉——刚羽化不久的寒蝉留在树上,等待着天气变晴。天一晴,属于它们的世界就会在长吟短唱里重新返回。
我也在等待天晴。这几天一直惦记着那群斑嘴鸭,想再看到它们凫游河面的样子,用镜头捕捉下它们悠闲的姿态。
是八月末的早晨与斑嘴鸭不期而遇的,地点在浦溪大桥,这里河域宽阔,有深水区,也有芳草浅滩,河面云影流动,两岸少有行人,是涉禽和游禽钟爱的栖息地。
最常见的是白鹭,每次来都能见到,当我站定,举起相机,其中一只就会拍翅飞起,另几只紧随其后,向上游飞去。
举起的相机总是落空,倒并不觉得遗憾,只要能看见白鹭在这里就好。这条河流原本就是它们的家园,我的到来是一种入侵,是对它们宁静生活的打扰。
来的次数多了,发现了一个秘诀——只要我远远地站着,不举起相机,就不会惊扰白鹭,它们自顾自地在浅水区捕食,在河边慢步、静立,神态安闲,有着天然的隐士气度。
白鹭捕食的时候很有意思,一改平常慢悠悠的样子,变得活泼,甚至有些滑稽,翅膀展开,在水里跳跃,拍打得水花四溅,看起来像一种欢快的田间舞。任何动物,包括人,在面对美食的时候,都会露出本真又可爱的一面吧。
在这里也见到过池鹭、黑水鸡、褐河乌、小鸊鷉。小鸊鷉善于潜水,看到有人过来就一个猛子扎下去,半分钟后,才见它重新浮出水面。
入秋后的黄昏,在这里会听到一种潜鸟的叫声——很可能就是小??的鸣叫,“嚯嚯嚯……嚯嚯嚯……”似一位少年歌者在重复练习颤音的发声法。这声音拉长了黄昏的时光,静立河边,看暮色潜入河面如同温柔的乡愁。
遇见斑嘴鸭完全是意外,或者说是上天赐予的惊喜。当它们——大概有七八只的样子,静静地泊于河面,我以为是附近村落游来的家鸭。
以前在河里看见的家鸭大多是白色,像这样麻褐色的也有,似乎又有些不同,羽色没有这么鲜亮。我打开相机,从长焦镜头里观看它们——墨色的鼻子,鼻尖嫩黄,翅膀上有一抹绿,翅尖又是白色的……忽然,安静的河面晃动起来,其中一只拍动翅膀,凌空而起,身边的伙伴也迅速跟随,拍翅离开河面,向高处飞去。
懊悔刚才那么好的时机没有把握,没来得及拍摄下它们飞离河面那富有动感的瞬间。
当斑嘴鸭从河面飞起的一刻,我脑子里浮出《迁徙的鸟》中主题曲的旋律。雅克·贝汉拍摄于本世纪初的这部纪录片我看过无数遍,主题曲烂熟于心,每个镜头也都深深地刻在脑子里。真幸运啊,能在自己生活的河边见到纪录片中的场景,仿佛实现了一个久远又念念不忘的梦。
这群斑嘴鸭很可能是浦溪河的过客,迁徙时路过这里,做短暂的休憩。
不知道它们会在这里停留多久,也不知道它们要去往哪里。秋天才刚开始,它们也是刚刚踏上迁徙的路途吧。
第二天,冒着细雨再次走到浦溪大桥,怀着忐忑的希望,把目光投向河面——河面空空,连之前常见的白鹭也不见了。
也许是下雨的缘故,下雨天,野外的小动物、小昆虫都会躲起来,就连随处可见的麻雀也没有影子了。谁会那么傻呀,下雨天又冷又湿,谁还在外面游荡。
下雨天也不是上路的日子,那些斑嘴鸭应该还没有离开这里。
雨断断续续下了一周,总算是停了。多日不见的阳光撕开云层,从裂隙里涌下,世界又恢复了生气。
拿起相机,起身离开居所。我要走进光里,走到田间与河边,走到那亮晃晃的地方去,让照着稻穗的阳光也照着我,让平凡与奇迹的野花铺满我生命的河流。
河流带来世界
连着几天没在浦溪河看见斑嘴鸭就会不安,担心它们被捕猎。这种担心使我对放网捕鱼的人警惕起来,眼睛盯着他,将手里的相机对准他,似乎这样就能把他唬走。
捕鱼人对我的目光浑不在意,穿着连身防水服,提着网,在河里跨步走着,把河水踩得哗哗响,嘴里还大声唱着歌。置身河流让捕鱼人忘记自己的年龄,肢体也变得灵活起来。快乐是有感染性的,尤其是孩子气的快乐,如果不是担心斑嘴鸭,捕鱼人这么快乐的样子应该也会感染到我。但是此刻,我对他的旁若无人很气恼,觉得他分明就是在挑衅。
河水已经齐腰深了,暮色里的捕鱼人低头弓背,身影酷似水怪。他通常是在天黑前放网,天亮时收网。谁知道那网里除了鱼还有些什么。或许捕鱼只是个幌子吧。
这疑窦让心里涌进一团团云翳,没有办法消除,就只有拉长相机镜头,在河面搜索,希望能看见斑嘴鸭的一家。
我没有看见斑嘴鸭,倒是看到另一种涉禽——黑水鸡。
对黑水鸡我并不陌生,以前住在太平湖边就看到过它们,池塘里贴着水面追逐,翻身扑腾,很激烈的样子,不知道是打斗还是在热恋。春天在秧田里也看到过,从碧青的秧田里钻出,田埂上叫两声,东张西望,很快又钻进秧田。黑水鸡周身羽毛青黑,只在两肋露出一线白,醒目的是额甲和嘴喙,鲜红欲滴,喙尖又是明黄色,像戴着一种特制的口罩。黑水鸡的脚很长,一看就知道它善于在沼地行走。当它进入水中浮游时,长脚就不见了,尾部上翘,颈部呈S型,完全是游禽的模样。
黑水鸡的体型比斑嘴鸭小一半,多数时候隐身在草汀里,如果不是拿相机当望远镜在河面搜索,很难看见它们。
是在一道河坝上游看见黑水鸡的,那里水域宽阔,水流平缓,几丛蒲苇草如绿色小洲错落河间。两只黑水鸡——应该是一对夫妇,正在营巢,游向一丛蒲苇,用尖长的嘴喙将苇叶扯断,衔着,再游回属于自己的营地——相距不远的另一丛蒲苇。
黑水鸡衔来的苇叶已经枯黄,这样不用费多大力气就能扯断。水面漂来的浮草当然也不能错过,赶紧衔起,送回营地。整个早晨,两口子就这么来回穿梭地运送着草叶,将蒲苇丛中间的巢高高垒起,河水淹不上来,它们就可以安然地在巢里生蛋孵蛋了。
将镜头对准那些蒲苇丛,仔细看,发现每一丛蒲苇中间都有垒起的草巢,吊脚楼一样。这个发现让我心里一阵欢喜,仿佛无意间窥见了了不起的秘密。
蒲苇丛间三三两两游着十几只雏鸟,其中一只见我把相机镜头对准它,咚地一下,潜入水下,水面随之荡开涟漪。雏鸟的警觉会相互传递,另几只也跟着纷纷潜入水下,很快又从另一边浮出来,见我还在,又潜下去,又浮出,像一群调皮的孩子玩躲猫猫的游戏。
这些雏鸟就是黑水鸡的孩子。黑水鸡是天生的潜水员,出壳后就能下水潜泳,这也是它们自我保护的本能,用来躲避从天空俯冲下来的猛禽利爪。
对黑水鸡秘密生活的发现,使我那被云翳笼罩的心又明亮起来。
早晨的时间过得很快,河面已有日光的倒影,该去上班了,收起相机准备离开时,空中传来熟悉的鸣叫,抬头看,一群大雁正在河流上空盘旋,站定,等它们落下,相继落入河中,才明白过来——它们正是我寻找数日的斑嘴鸭。
斑嘴鸭的数量没有像我担心的那样变少,而是更多了(有二十多只)。不知道之前看见的那一家子是否在其中。我愿意相信它们就在这支壮大起来的队伍里,等待着更多的伙伴从四面飞来,集结,等待着秋天最后一声号角吹响,沿着祖先迁徙的路线,向着更温暖的地方启程。
端起相机,对着河里的斑嘴鸭按下快门。在离斑嘴鸭不远的地方,捕鱼人穿着连身防水装,提着湿漉漉的渔网,正从河里走上岸。不知道他是否有收获——应该是有的,就算没有收获到鱼,也收获了快乐,或许他每日最快乐的时光,就是这一早一晚下河放网的时光吧。
居住的地方有一条河流是多么奢侈的事,如果这条河宽阔又清澈,那么一生守着这条河也不会觉得单调匮乏。河流会带来整个世界的讯息,季风流动,云起云散,还有“飞鸟相与还”的晨昏,每一天的遇见都不可预期,每一个平凡的瞬间都隐藏着奇迹,如同生命本身,不能复制,不可重来。
(选自《安徽作家》,2022年第三期)
作者简介

项丽敏,中国作协会员。居于安徽黄山,自然写作者,已出版《闲坐观花落》《山中岁时》《浦溪河的一年》等十余部散文集,多次获安徽省政府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