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5-05 来源:安徽作家网 作者:安徽作家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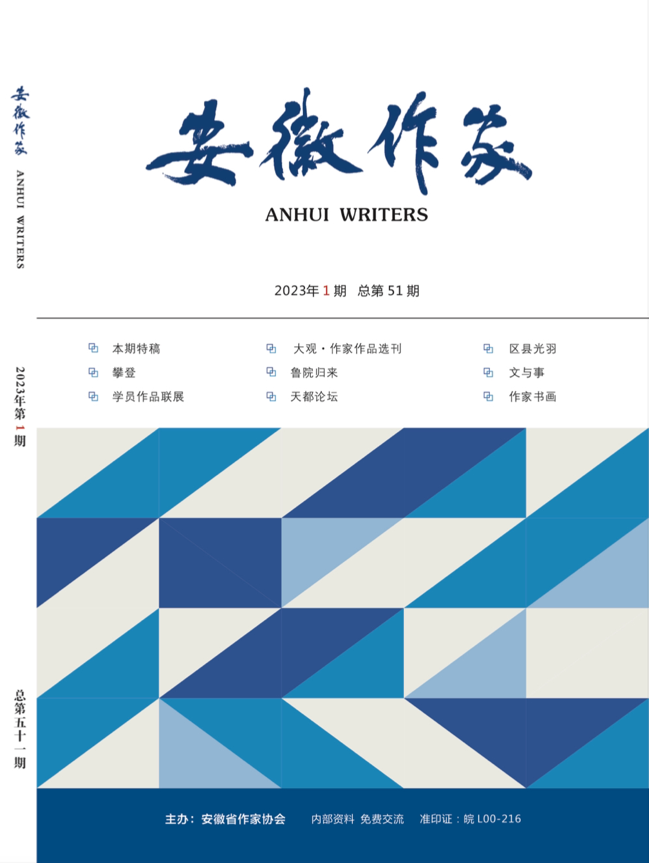
泾 江(节选)
张向荣
一
这是一条江吗?
在我的想象中,被称为江的水域,一定是水势汹涌、波翻浪滚。
当双脚站立在横坝头的桥上、看着从横坝头身边穿过的波澜不兴的那片水域,我不禁心生疑问:这宽不过数十米、长不过几十里地的水域,能叫江吗?它的气势与江太不相称,称江让它有些名不副实。
它的的确确有个叫江的名字:泾江。历史上,它的名气并不小,还有过“泾江口镇”的行政区域设置。
泾江所在的位置,在今天的宿松县洲头乡。北起后湖,南至洲头集镇,穿过西口、坝头、官洲、下夹、金坝、洲头等村。
从百度搜索,“泾”的本义:由北向南、由高向低流动的水。根据此解释,我们知道它为什么叫泾江。
最早的泾江,是连通后湖与长江的水域,湖水由此可以从北向南、流入长江。
不过,泾江是古称,现今的年轻人知道这古称的不多。
今天的人们,将泾江一分为二,分别称为坝头港、洲头港。
港,在词典里的解释为:江河的支流。
二
说到泾江,不能不提及石良这个人。
石良,宿松九姑杜溪人。生于1319年,殁于1394年。早年,他在家乡所在地召集义勇,筑城设寨、屯田养兵,以保境安民为己任,也深得一方百姓拥戴。
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明太祖朱元璋率兵攻克江州。石良闻讯后,立即率领所属义勇奔赴江州归顺。太祖自然兴奋不已、赞赏有加,立即授他为统兵元帅,留镇宿松。
1363年8月,鄱阳湖大战开始。一开始,朱元璋处于劣势,很是不安。正在他一筹莫展之际,朱升为他生出主意:陈友谅此次为取得鄱阳湖大战胜利,倾巢出动,人多势大,但粮草必定难以为继,肯定坚持不了多久,只要堵住南湖嘴,断了他的退路。在他粮尽力疲之时,前后夹击,肯定能取胜。朱升这一说,自然有道理,朱元璋听后,也说:陈友谅粮草难以为继,我的粮草也跟不上呀!可他很快想到了距此不远的石良,觉得他忠勇可靠,便立刻派俞通海到宿松向石良求援,并传出“谁送粮,封宰相”的口谕。
石良见到俞通海,知道朱元璋担心陷入困境,立马着手粮草的组织筹备。为了开辟一条直达长江的快捷通道,他亲率部下三千人,开挖出一条长达三十余里的新沟,直通长江。新沟告成,运粮送草的船只络绎不绝地奔向鄱阳湖,缓解了朱元璋的燃眉之急,也为后来朱元璋与陈友谅抗衡、最终战胜陈友谅奠定基础。
石良率众所开挖的新沟,就是“泾江”。
关于这段史实,《宿松县志》(民国十年版)载:此江为“明初鄱阳湖之战,邑人石良督义兵,为俞通海开沟三十余里,引大河达泾江口入江”。
从这一记载,我们看出,泾江是一条人工河,或者说,是一条人工的运河。泾江与石良这个名字是连在一起的,没有石良,也就没有泾江。
因为泾江,因为运送粮草有功,石良才有后来的“田园宰相”的封号。
不过,关于石良率众开挖泾江一事,有一点值得商榷:曾有人撰文称,石良当初率部三千开挖泾江,一日便告完工。其实,三十余里的泾江,宽的地方数十米,窄的地段也有四、五十米,不说是三千人,就是三万人,恐怕也一日难以完成。这“一日”之说,或许是文学上的夸张,当不得事实。
看到现在的泾江,我揣测:当初的开挖,要么是在原有河道上的疏浚,要么是组织了大量的人力,不然的话,这浩大的工程难以在短期内完成。
再者,在石良之后,是否开展过后续工程的实施?
遗憾的是,找不出史料证据,只能是姑妄言之。
三
现在的泾江,依旧未改当初的容颜:河道不见变窄,走向不见更移。
碧水悠悠,微风鼓浪。
“沧海桑田”的变化,在这里似乎放慢了脚步。
六百多年的时光,并未在这里留下多少印痕。
早年,发挥了重要军事作用的泾江,后来因通江连湖,有舟楫往来,为人们的出行和商贾带来诸多便利。
因为泾江的便利,向来喜爱依水而居的人们,纷纷在两岸筑室造屋,一个个村落和集镇相继形成。
坝头、下夹、洲头……这些集镇不仅没有衰落,相反,日益焕发出勃勃生机。
今天的泾江两岸,绿树摇曳,繁花似锦,一栋栋漂亮的楼房排列有序。居住的人们,静享绿水滤过的清风和生产生活中的方便。
从有关资料,我了解到泾江口的几次变化:为了防止水患,清顺治五年(1648),泾江口一度被堵塞。康熙二年(1662),为了舟楫之便,重新挖开。到了光绪十一年(1885),泾江口又再次被堵。此次不仅堵塞,而且还在上面筑了堤,与上下的堤坝连成一体。
从这以后,泾江被彻底堵死,切断了与长江的连通。
泾江,不再是一条支江;泾江,不再通航行船。泾江,成为一片静静的水域,仅仅与后湖相通。
泾江通航行船的历史前后也达500余年。
如果你想去看看泾江口,去老洲头转转,不用他人指点,自己也能很轻松地找到。
当然,你只能在同马大堤内转,同马大堤外,是见不到一点泾江口的影子的。
四
在位于泾江口的同马大堤上,如果天清气朗,可以望见隔江不远的江西湖口县城。
湖口,因古彭鑫湖得名,还是鄱阳湖得名?透过历史的帘幕,我们可以想见,当年泾江口外一片汪洋,江水翻滚,奔腾不息。从这里抵达湖口、进入鄱阳湖,真的是太方便了。
或许是因为距离湖口太近,当年的朱元璋为截断陈友谅的退路,除了在南湖嘴设伏外,还选中了此处,最终使陈友谅命丧泾江口。
翻开历史的画卷,朱元璋当年与陈友谅在鄱阳湖血战,前后达四个月之久,此战可以说惊心动魂、悲壮激烈。
应该说,一开始,陈友谅人多势众、战船体大坚固,是占上风的。可经不住屡吃败仗,被朱元障打得丢盔弃甲,以至渐渐处于下风。
经过数月的搏击,陈友谅所剩的百余艘战船残缺不全,再也天法投入战斗。陈友谅知道败局已定,便想到突围逃生。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八月二十六日深夜,陈友谅命张定边率众出鄱阳湖向长江突围,而他自己也脱下龙袍,摘去冠冕,手握开山大斧,站立在舱板上,作最后的拼死一搏。
得知陈友谅将深夜突围,朱元璋迅速率部追击。陈友谅的部队且战且退,好不容易冲出湖口,来到泾江口,岂料到,在这里潜伏等待一个多月的朱元璋部队,立即从茂密的芦苇丛中杀了出来,一时间,颦鼓齐鸣,杀声震天,陈友谅腹背受敌,仍不甘心束手就擒。他站立船头,手中的开山斧左砍右劈,企图杀出一条血路来。殊不知,当他准备跳上一条小船逃跑时,“噗”的一声,一支利箭飞来,从他的左眼贯入脑颅,“咕咚”一声,仰面倒在舱板上,身子扭了几下,便两腿一伸。
陈友谅再也无法圆他的皇帝梦。一代枭雄,怎么也不会想到,会被乱箭射杀,丧命于泾江口。
陈友谅死后被手下抢出,后归葬于武昌蛇山。
……
风吹老家
刘鹏程
我是在一场秋风里去的老家。
回到老家的时候,屋场上虽然很杂乱,落叶满地,但是因为北边紧靠着的那一大片树林子,遮挡着风,所以显得很安稳。我端一把小凳子在老屋的门前坐下来。见我回来,一些老兄弟和叔子们,三三两两地聚过来和我聊天叙旧,有的手里牵着他们的孙儿孙女。一些稍大的孩子,也不认识我,从我面前闪过,便迅速地消失在老屋的拐角处。
说话的时候,听屋后树林子里传来阵阵风声,以及风过树叶的声音,舒缓而安详。哥嫂在厨房里忙乎着,为我准备丰盛的午餐,屋顶上飘着久违的炊烟。仿佛回到了从前的时光,令我感到无比温暖和亲切。
因为是在湖边,风往往要比其它地方稍微大一些。在我的记忆里,老家就是在风中,我就是在风中长大,然后离开老家的。而正是因为风,定格了我关于老家温暖或清凉的记忆。
在初夏的时光,就是这风,让大片空旷的麦田动起来,像一块巨大的布匹,在我的老家和我的内心里飘起来。黄昏的时候,我骑在牛背上吹着麦哨,缓缓地走在风中的麦田,回家。
母亲的炊烟也恰是在这时候从屋顶上升起来,然后在风中飘散。炊烟在风吹散之前,在天空中总要划一道优美而柔软的曲线,有时候舒缓,有时候迅捷。后来,我在城里也爱上了读读或者练练书法。这时候我就想象,母亲就是我最喜欢的书法家,炊烟就是她的书法作品。我不知道一生慈祥的母亲是否也有内心激荡的时候。否则,大风中的炊烟为什么会像一幅狂草的书法,悬挂在老家的天空,和我的内心?
当然,春天的油菜花在老家的田野上铺开的时候,往往风就停止了。我不知道这是天地的做法还是因为什么别的。要不,风就是被人们收敛在的内心里了,等到漫天的油菜灌浆、结籽了,才吹出。
风在湖水之上就是又一番样子。小小的春风把浅浅湖水吹起波纹以后,湖水就开始涨,鱼虾、蚌壳在水下开始活跃起来。而冬天的风呢?吹起白浪的时候,渔船就开始靠岸,倒扣在湖湾的浅滩上,等待另一场春风的到来。
而在天上,风总把老家的云吹起又吹散。一些云朵在风中,在天边,像变换着的家畜、家禽。这时候,天和地就融为一体了,它们自由地游走在天地之间。这算是村庄最吉祥的象征了。
我这是坐在老家的老屋场想象那些过去的时光。其实老家现在正在快速地变,变得很快,像一阵风。我们的村庄已经迁到不远处的马路边了,一些小楼房在汽车掀起的尘埃中,有规则或者无规则地排列着。这个原始的村落,世代沿袭的村落,即将废弃在这里。
这风大概是从城里吹来的。联想到时下,先是一些城市喜欢建新城,把幸免拆迁的老城留在那里,等待老去。散落在老城的,是一些城市贫民。他们缓慢而安详地生活在这里,仿佛时光的深处。这场风很快吹到了乡村,我的老家也不例外。
这次回老家,我就看见新村的小楼房大多门是锁着的,因为青壮年男女都外出打工了。只有一些老人带着小孩,他们依旧居住在旧屋场的老房子里。只有等到过年的时候,孩子的父母们打工回家,才回新家里住上一阵子。旧屋场的老房子大都居住着爷爷奶奶级的中老年人。其实他们大多乐意继续住在旧屋场里,一是因为不住在儿子儿媳一起更自在,二是因为他们住惯了老房子,习惯了老地方。
每次回老家,在内心里我始终不习惯住在侄儿们居住的那个路边新村。那个破旧了的老屋场——我童年居住的地方,才是真正的老家。我有时候甚至不太理解他们,住在泊湖水的近岸边好好的,还有一片原始树林子围绕着,依山傍水,为什么非要搬上去呢?
我不喜欢现在的这个风。无论是我现在居住的新城,还是老家现在的新村,风总是带着厚厚的尘埃。
现在,老家的一些老房子开始败落,甚至倒塌,只剩下一堵堵土墙。一些曾经繁华的大户人家的院落,长满茂密的茅草和灌木,偶有猪狗在此出没。
老家就这样,像我的这些老兄弟老叔子们,顶着一头白发,在风中,在空旷的田地里,孤独地杵着一柄锄头。当我以后以一把骨头的方式回到这里的时候,估计老家也要消失了,只有风从上面吹过……
既是乡愁,也是归家的路
吴云涛
小时候,正月里,母亲都要带着我们去外婆家。我们沿着茯苓畈蜿蜒的洋马河,一直往前走,就能望见一个叫堰岸上的村庄。我的外婆总在村口的大柳树下等着我们。寒风吹动着外婆的白发。
我的家在安徽省宿松县,这里曾经是古松兹候国,有着两千多年的建县史。这里,有着许多像堰岸上一样的村落。小小的村落,是宿松游子最思念的地方。
游子思乡,想起自己的村落,最不会忘记的又是村落的名字。家乡村落的名字总是那么温馨和甜蜜。每一个名字,仿佛是游子心中的一首童谣!
家乡在长江北岸、皖鄂赣三省结合的地方。据《宿松县地名录》统计,全县有近5000个自然村。这些村落的取名,或依据地形地貌,或依据居民姓氏,或展现一段历史,或展现民俗乡风,千姿百态,各具风韵 ,构成独特的乡村记忆。
村落以地形地貌取名的最多。一般在山区和丘陵区,村名尾字多有洼、垄、坡、岭、宕、叉、湾、冲、坳、尖、山等。如:陈汉乡的骑骡尖、打杵叉、烂泥垄,北浴乡的乱石壳、筲箕坦、锅川石,隘口乡的剪刀石,二郎镇的石竹沟,凉亭镇的缸钵洼、燕窝地、蟹子夹。这些村名拙朴、形象、生动。洲区和湖区因为地势低,多水,村名的尾字固多是墩、营、圩、埂、湾、港、坝、湖、渡等,例如张墩、桂营、史家营、石坝、罗渡。比起山区和丘陵区,洲区湖区的一些“姓氏+地貌”式的村名少一点灵动的趣味,但却同样包含着厚重的人文和历史。例如,汇口镇以营为尾字命名的村落多,是因为明朝初朱元璋的军队曾经在这里安营垦荒;宗营,就是安营的宗姓军人诸多。
有一类村名,显示了久远的乡村历史文化。这些村名一般都有着优雅的画面感,和有韵律节奏的动感。如柳坪乡的风古屋,陈汉乡的滴水岩,隘口乡的甘露坡、风声村、望云冲、过矶石,孚玉镇的桐子园,华亭镇的白露窠,许岭镇的秋藤村,佐坝乡的渔雁村等,村名背后都有一段故事。华亭镇黄大口村有刘家篱、张家摆、古岭曹等村落,名字都有较强的地域风味。在陈汉乡,有鸡鸣冲、白鹤冲、虎踏石、官堰头等,几个村落连在一块,透着浓浓的山间野趣。
一些村名讲述的乡间故事十分优美。陈汉乡的九登山,讲述的是五祖寻母九次登山的传说。陈汉乡的上马石,讲述的是本县“田园宰相”石良从这里上马西征的故事。汇口镇的归林村属古彭泽的域地,东晋诗人、彭泽县令陶渊明在这里作《风阻规林》二首,“归林”即“规林”。佐坝乡的得胜山是一个小渔村,属横路洲。这里是有名的古战场,是朱元璋训练水兵的地方。元末明初,这里发生过惊心动魄的战事 。五里乡的南台山曾是唐朝闾丘县令为诗人李太白筑台读书的地方。
古老的村名,连同历史的风云,载入了史册。如仙田铺、太子庙、杜溪屋、枫香驿、沙塘陂……仙田铺这个村落在2380多年前就已经得名了。追索到西汉高后四年(公元前184年),始置松兹侯国就在“仙田铺”。仙田铺古老而厚重的历史,称得上是国宝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沙塘陂,在县城以东,因李白《赠闾丘处士》有“贤人有素业,乃在沙塘陂”的诗句而留名。太子庙也有600多年的历史。梁朝昭明太子编纂《文选》伴随着游历,使得他在中国多地存有文化遗迹,其中包括宿松。明熹宗年间,宿松民间流传昭明太子在葫芦坡下显圣,于是有乡绅牵头建起了一座庙。这座庙就是太子庙。清朝有两位宿松籍的翰林院编修石葆元、朱书都有诗文予以记述。
游子心心相念的是故乡的村庄。宿松的自然村落的名字,许多都显得粗糙,俚俗,率性。这些个性张扬的名字显示了顽强的生命力。隘口乡有个村落叫懒牛退轭。牛轭是耕地时套在牛颈上的曲木。这个村名很显风趣幽默。华亭镇有狗尾欠、苦岭咀、坟峦屋、驼背树屋、吴家破屋这些自贱之名。把宿松这些自贱之名的村落疏理岀来,也很有意思。其实这些屋场里多有书香门第、耕读世家。隘口乡的古山村落,至今民间还是称之为估亩山。传说古代粮官丈亩到此,山路崎岖,难于清丈,便登山估亩,因此得名。华亭镇的先觉岭,老百姓口里还是“酸脚岭”,形容岭太长了,走到这里脚就走酸了。也有雅俗共赏的,如华亭镇的雪山洼,地处横山腹地,冬季积雪时间长,故名。还有长铺镇的鹅公包、泥里鳖,河塌乡的黑漆门楼,程岭乡的黄鳝咀,汇口镇的快活岭,名字俗,却顺口。宿松还有的村名因时间久远产生讹传,如保持畈原为宝池畈,乌池村原为污池村,韩文岭原为寒梅岭,等等,当然也可能是因世情而变。
宿松是中国诗歌之乡。诗意山水,钟灵毓秀。我工作第一站是一所山区小学,坐落的村子叫南屏庙,也称过乐灯村,我更喜欢南屏晚钟的南屏。这里还有轿藤、衔柴这些有趣的村名。我小时上学要经过的竹峦窠,掐野菜时到过的红旗营,为住校的弟弟送菜走过的白子口,去爱人家要穿过的连牵塘,一个个小村落都是那样亲切、动人。我喜欢大山深处的燃灯寺这个地名,这是我父亲读私塾的地方,寓意用知识点亮光明。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城镇化的进程,家乡的一些村落已经消失了,然而作为乡村文化的记忆,村名依然存在。我特别喜欢用乡音来喊我家乡村落的名字,乡音乡韵,格外沁入心扉。希望一个个饱经岁月沧桑,从悲苦、欢欣中走过来的村落的名字,能给家乡带来美好的福祉,光明的未来。
草木乡村
余芝灵
今年大半年,因为对故乡的牵挂,一次又一次地往返于乡村与城镇。乡村濡养了我们。住着住着,人是真的住静了。许多时候都感觉自己无欲无求。只想静静地在乡村住到白发满头,住到天荒地老。好像自己原本就是乡村的一分子,是一株草木,一滴露,一粒鸟鸣,一声蛙鼓,甚至一匹流水,一米月光。此外,还能是什么呢?有时会感觉尘世中的一切,都离我很远,远到模糊。人们在争什么,抢什么?他们争,他们抢,又与我何干?我只想安静地享受这一切自然的慷慨馈赠,和家人共度余下的岁月。
早上四五点,黎明即被鸟声啄破。它们大约是衔了一万粒的珍珠,一粒一粒地往外吐。所谓口吐珠玉也。总有长长的过门,有复调,有回音。其婉转清越,真是难以用语言形容一二。那些到底是什么鸟呢?老实说,我也认不全。而鹧鸪,那是一定有的,行不得也哥哥。布谷鸟。斑鸠。麻雀。其中尤以一种尾巴特长特好看的鸟儿叫得最欢,最悠扬,应该是蓝尾山雀。仿佛它长着这样一只尾巴,不唱好歌儿,就愧对了它。它是每一根羽毛都拖着美妙的音符。果然,它是没有辜负的。我们总是在鸟叫声中醒来。有时,舍不得醒来,就又悠悠睡去,或者假装睡去。希望它只是个梦,要让它长些长些更长些,最好不要醒来。它们的歌声,是一天唱到晚的。只是在早上,格外的清新格外的魅惑。如塞壬的歌声。你不沦陷,都得沦陷。
正午的花朵,我想应该是最美的时辰。它们抖落了早晨的娇羞,又被日光沐浴了一整个上午,到了正午时分,精气神都到了极致。如果你恰巧在这个时分去看望它们,我想,它们一朵朵都怀抱爱情,静静生香,情意绵绵。就像是听到了清越的笛声。
傍晚的云霞,时刻都在变化。所谓波谲云诡也。瞬息万变。“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再恰当不过了。只是这雪,有时是白雪,有时是五颜六色的雪。最喜欢傍晚徜徉在美丽的山道上。看瞬息万变的云霞,在天际翻滚。你想象它们是神马,就是神马,是乌龟,就是乌龟,是绸缎就是绸缎,是壮丽河山就是壮丽河山。你自己也可以轻盈成一朵云,一只舟子,在广阔的天际里遨游,展开鲲鹏一样的翅膀。那缤纷的色彩,那千奇百怪的形状,那流动的姿态,你有时会泪水盈眶。你会感动于它们的织锦裁缎。它们可以是任何什么。只要你愿意它们是什么,就可以是什么。它们是你温驯的牛羊,也可以是桀傲不驯的烈马。你可以赶着它们回到家园,也可以骑着它们在辽阔的天地之间纵横驰骋。一万个傍晚,就有一万种的云蒸霞蔚。它们最后都要落到夜的幕布里头去,将无边无涯的翅膀合拢,成为温顺的夜的骄子。
每天夜晚都会有大合唱。虫子,青蛙,夜鸟,以及一些不知名的动物,不知名的植物,甚至天上的星星与月亮,都会参与。它们或在天光里,或在月光下,各各争相献艺。而远山模模糊糊的影子,与远远近近的几点灯火,总如梦幻一般,一直在照着回家的路。走在这样的路上,总像是喝了七分醉的酒。总是舍不得回去。愿意今宵复今宵地永远延续下去。没有月亮的夜晚,有时美丽甚于有月。一切都如梦如幻。如前生,如后世。看到的,听到的,望到的,都不真切。你常常疑心自己并不活在这个世界,这个世纪。或许是走在远古的一个什么朝代。一切都是屈原离骚里的那个样子,香草即是美人,美人即是香草。每一种植物的香气,都在夜里升腾。你不用使劲吸,它轻轻巧巧就进入了你的五脏六腑,清洗你的心你的身体。你常常像是在接受一场洗礼。像是在庄严的教堂,亦像是在接受剃度。从此,你要洗心革面,做一个全新的人。前尘往事,是可以悉数丢弃的。什么都算不了什么。只有这满耳的天籁,让你沉醉,不知归途。你可以看到大块大块的天,看到满天的星星,与浑圆的月亮。
大白天里,你可以随时去拜访任何一种植物或动物。它们都会以一种明媚而又热切的姿态来迎接你。是的,任何时候。你可以被一只蝴蝶引领,而改变一天的灵魂走向。你也可以随着一朵花,一起走过梦幻的黄昏,感受它的悲喜与生命历程。和它们一起笑,一起歌,一起舞蹈。你也可以跟着母亲,去看看她的田园,去跟她一起听菜们的呼吸与拔节生长的声音。流水一般,有啪啪的节奏。很清丽的样子。只要你附下身子,你总可以听到它们欢悦的鸣叫。既像写诗,亦像作文。而更像是一位位娇羞的少女,粉面含羞。一个劲地窜着个儿,长着窈窕的腰身。既养内,又养外。饱含汁液。
真愿意从此一直住在乡下,做一株寻常的植物,或者一朵天马行空的流云,一只在树上唱歌的鸟。或许,哪一天,我就真的彻彻底底住在乡下。做一个彻底的乡下农妇: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这可能是奢望。也不尽然。如今乡村公路都是村村通,路路通,户户通,再不是过去的羊肠子小道,再不用肩扛手提。条条道路通向城市。我们如何不能在乡下长年住着?
如果没有乡下,我们到哪里去寻找自己?如果没有乡下,我们何以知道自己的前世今生?如果没有乡下,我们如何懂得——其实,芸芸众生,都不过是一株普通而又再普通不过的草木。汲天地之灵气,与日月之精华,修炼成每一个独立而又迥异的个体。
选自《安徽作家》202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