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5-12 来源:安徽作家网 作者:安徽作家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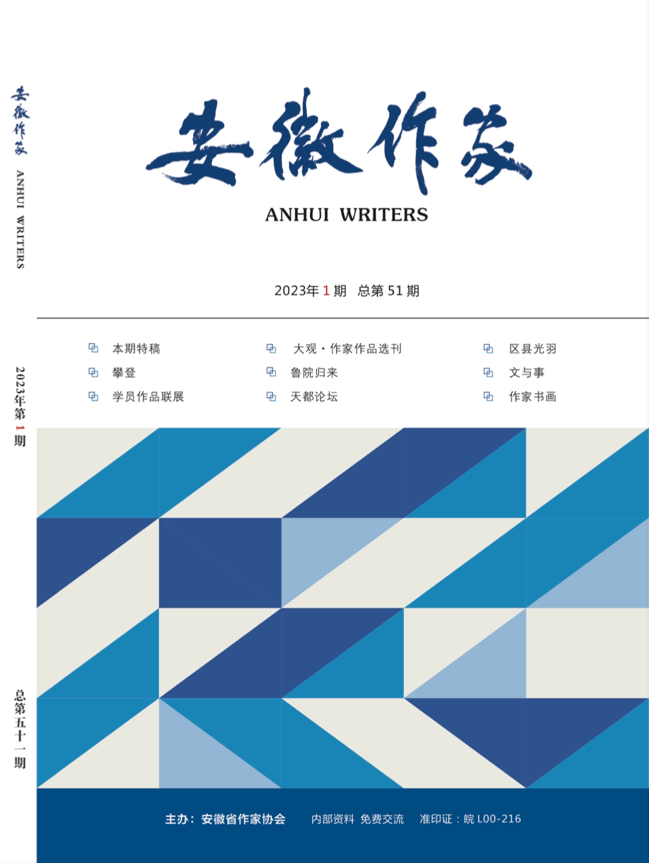
找个能说一吨话的人
雅不知
一吨话是多少?
八十年代初期那两年,诗人张枣每每大老远跑去寻柏桦。二十年后柏桦回忆说,每次我俩都要说上好几吨的话,我们将这样的见面称之为谈话节,但不能超过三天,不然就会因说得过多而窒息。说话的长度是有重量的,这是一个好的比喻。我想,也要考虑到人的体力,如果是林黛玉,一吨话也就是极限了,大约是十个小时吧。
黛玉在荣国府的日常生活,虽然她素性淡然,也不免时常要到各处走走、坐坐,说一会子话的。每次在贾母处,因奉承的人多,有她的话时,不过说个十二三斤吧;在王夫人处,也就是三五两。和姊妹们之间,说个五斤七斤算好的了。这样计算的不光是长度,还有密度。总归离心越远,话就越轻,离心近时,话自然沉一些。
四十二回以前,黛玉和宝钗说话,也是轻的,但毕竟才学相敌,多了一层较量的心思,比起姊妹们便重一些,一次也大不过二三十斤。后来“蘅芜君兰言解疑癖”,不想二人竟成了贴心人,有几次谈话,说到二三百斤的重量。这是作者的菩萨心肠。有时和紫鹃说话,话是重的,但黛玉性冷,话不会多。偶尔一日,会说到四五十斤,这样的日子,一年不会有一日,平时不过三五斤罢了。其余的,老嬷嬷有二斤,雪雁一斤,春纤三两。但紫鹃每天或有三五百斤的话想要说给她,只是说不出来。黛玉和香菱,在教授写诗的那一段时光,她的讲话是用心的,用的是菩萨心和夫子心,故话沉,最多一次,百斤而已。其余说的话,每日加起来不过一斤。
能一次说上两千斤话的人,宝玉一人而已。两小无猜时,起居都在贾母外间碧纱橱内,每天有几个小时的话可说,虽然话尚不沉,但长度不短,日常已能达到数百斤。后来年纪大了,住的渐渐远了,说话的机会有些减少,但心反而越来越近起来。有时即便相对静默,已是互知心音,无声处却胜有声,悄然间话已百斤百斤地产生了。黛玉遇见宝玉,说是前世的缘纷,不如说是今生的福报。知音难求。如果没有林黛玉,就没有贾宝玉,只是世上多了一位富贵闲人罢了;如果没有贾宝玉,就没有林黛玉,只是世上多了一位恹恹才人罢了。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真的有幸遇见时,各自的人生才得以放大,也许生死离别,竟都是小事了。说《红楼梦》是悲剧的,有着人心的不满足。 《红楼梦》讲的是人的孤独,也是讲知音的难觅。
才学相近的,未必能成知音。黛玉与宝钗,一时瑜亮,也只是做到能贴心而已。 性情相近的,未必能成知音。黛玉与妙玉,都是清冷孤高的性子,也只是做到相惜而已。 情感亲近的,未必能成知音。黛玉和紫鹃,紫鹃可以和她托以生死,却也不是知音。 身世相近的,未必能成知音。黛玉和香菱,黛玉怜她孤零一人存于世间,也只是尽心对她,毕竟不是知音。 疼惜你的,你疼惜的;了解你的,你了解的;敬你的,你敬的,都未必能成知音。如贾母,如晴雯,如湘云,如探春,都称不得是知音。 人之相处,最难的,是知字。难上加难的,是知而欲近,近而生情,一往而深,这才是知音。
知音最难得。古来的传说故事,最好的几个里,就有“高山流水”这一篇。“高山流水”最先出自《列子?汤问》,传说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志在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钟子期必得之。子期死,伯牙谓世再无知音,乃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
我曾上终南山,山上一处处多有住山隐居的人。看见一间门上有残了半边的春联,写的是“知音说与知音听”。我想那些住山的人,心思原该是极淡的了,还这么牵挂着。我才知道,对知音的企盼,未必是俞伯牙、林黛玉这种绝世之人独有。后来看到刘震云先生的《一句顶一万句》,通篇都在讲人的孤独,原来我们这些普通人,终生也都在寻觅一个能说得上话的人呀。我们不能确证这种寻觅。这个心底的秘密,中国人只是从来不讲给其他人听就是了。
最忆牵牛花
杨 秋
初冬将至,花木草禾渐次失了水分,日见枯黄,显出苍凉的光景。
那些耐寒的花除外,比如牵牛。这花形容娇嫩,吹弹即破,却又极抗风雨。它的颜色也丰富,有白、紫、蓝、浅红、深红等。深红的俗气,浅红的惨淡,看到紫色总让人想起深紫的绒布来,毛茸茸的,倒也可观。蓝的最普遍,在长的秋草里隐藏着。仔细看过去,越发多起来,很有些意思。
郁达夫先生是偏爱这种颜色的,他称蓝色并白色,在牵牛花中属上乘,我也认同。去年一次湖边漫走,看见一棵缠绕在枯枝上的牵牛,开着白的朵子,玉一般细腻柔嫩。忽而感觉,这白色是牵牛花中的贵族了。可惜得很,第二日再去,已被连根拔去,细藤上还缀着两三朵,与昨日相比,细瘦了许多,也没有了白玉的光泽。
这似乎成了一条规律。每个秋季,在小区的石楠棵旁、木栅栏边,总有一些牵牛花的细茎,不知什么时候攀了上去。在清晨的冷风里,开出蓝的、紫的朵子。风一过,这些蓝的紫的,就像妩媚的眼,闪着快活的笑意。
目光触及到它们,总莫名得紧张起来,担心它们此后的命运。接下来几日,自是不敢再去。或者怀了侥幸之心,悄悄去望:半死的藤上必缀着极为惨淡的小朵,那努力的样子,叫人不忍。是我目光有毒,还是谁窥到我的欢喜,而剥夺了它的性命?似乎都不是,却又出奇得准确,不知是何原因。若开口询问,必引来诧异的目光,仿佛在说,为一棵野花?往往自己倒先失了底气。
几日前去乡下,经过我的村庄。我执意停留一会,一个人。这个村子几年前被拆迁了。所有的树木,成材的、不成材的,一律伐掉了。剩下新发的野树蓬、过膝的荒草以及随着地势起伏的暗淡陈旧的绿植。
我艰难地在荒草中行走,寻找当年生活过的痕迹。目之所触,一片荒凉。我感到如此陌生,有种被撂在荒岛的惶恐。所幸,在一片结满籽的秋草里,看到有蓝的紫的亮光在闪,“牵牛花——”我眼中一热,几乎要跪下去拥抱这片土地。这里应该是我生活了二十年,又离开了三十余年的家。
牵牛花盛开的所在,是我家厨屋之南,紧挨着水坑。那一年不知是从飞鸟嘴里跌落的,还是风送过来的种子,在坑沿儿柳树旁生发了长长细细的茎,随着树身向上攀援。心形的绿叶带着三个尖儿,在南来北往的风中不停颤动着。入秋之前,柳树的细条子上点缀了蓝的紫的粉的花子,为绿枝增添了美好。
放早学回家,掀开馍筐子,坏红芋的气息夹着馏熟梅豆子特别的味,让我没有半点食欲。母亲总是这样子,发觉东西坏了,不扔。用刀削了又削,剜除坏掉的部分,仍旧做给我们吃。不变的,还有同时出锅的梅豆子,它和坏红芋的气味混到一起,我毕生不忘。
那满是绿肥和尘土的水坑,似乎无声地滋润着那棵柳树,连同缠绕的牵牛。入冬很久,桐树、楝树、枣树,它们的叶子落净了,大柳树依然繁茂着,顶着一头彩色的花。对着这样的景致,我忘记了坏红芋的气息。那棵绿柳以及攀附的牵牛,成了我心中的牵挂。
又一次回家,书包一丢,就去看。眼前的状况让我惊骇:心形的绿叶全折皱着,向下垂,有少数花在开,形容憔悴。三棵小拇指般粗细的根被齐齐割断。我搂着大树把脸贴在缠绕的茎上,感到心里很疼。
母亲说,那棵树是公家的,我们不能阻止谁干什么。我知道,除去我之外,谁在乎几棵野花子呢。手里的镰刀,随时可以让它毙命的。不曾想牵牛花居然落下了后代,一年一年,生生不息了。
凭借着匍匐在地的牵牛花,我找到了我家的堂屋、西屋、父母住的小屋还有厨屋,以及院子里那棵大泡桐树、堂屋后的棠梨子树、西屋前的两棵枣树、压水井、鸡窝……鸡窝边上,天麻正开着银红的花。
那道矮墙地基处,绿植要高出一些。墙外杨霞家青砖的堂屋、向西连着厕所的过道、门向东的厨屋、院子里那一棵椿树上绑着布带的小臭,瘫坐在木墩上咿咿呀呀的,不知道是哭还是笑。
程老太红着脸膛子,拎着拐棍仍旧在她的园子边逡巡;大老陈倚着老槐树端着小馍盘儿吃着红芋。他们各做各的事,没有人看到我。我用半天时间,在村子里走了几趟,感觉自己像是一个外人。
站在涡河坝上,再看,一片荒芜罢了。
为了解决心的思念,我从故乡的荒草里,寻了牵牛花的种子,埋在花盆里。来年,出了两株可怜的芽,很委屈地生存着。我时时关注着它们,其中一株无端黄了。另一株长长了秧子。我用细的线把它缚在防盗窗的网上,竟然沿着网格跌跌撞撞向前爬了。随着晓风晚风,心形小叶子微微颤动。很细的一枝,也没走多远。
夏里,酷热的太阳炙烤着它,夜间吸纳的清凉,全被烤走,整个藤叶若水烫一般。如此,一天一个生死轮回,却也活了下来。一届仲秋,细藤上有了花的蓓蕾,我们等着它盛放的样子,始终不得。往往开了一半,大太阳一照,匆匆拧在了一起。
内心只觉着它可怜,牵牛花没有留下一粒成熟的种子。以后,我也没有再种过。
故乡(外二首)
马金萍
槐花提着一串香
在梦中
邻家小妹又开始唱了
相思高过思想
不知道那个曾经的木马是否变了模样
想你的澎湃
比这里的早会还要热烈
打卡,草稿,报表
像极了你的笑
无时不刻
乡间的小路
成长在远方
从未停止过坑坑洼洼
我枯萎,我茂盛
似一个从未休息的陀螺
童年的田间有一棵树
路边的杂草又似多个我
路啊,
走过祖辈,父辈,如今又走过我
羊肠一样的弯
朝夕相照,风雨婆娑
偏爱这样的
想做一个长长的梦
有浩雪,有繁花
有弯月
还有那片无忧的羊群
绿色传染了绿色
我没有告白
就这样,跟随了一片绿色
我把自己分成两半
一半是我,一半是影子
高处,低处
我们身嵌其中
一片片的
不再消失
山路肥沃,等浩瀚的秋景深过春宵
慢慢活着吧
绿,毕竟代表生命
就当一次复活
初冬晨练(外一首)
丑 石
我看到了芦苇,高高矮矮,参差无味
单调轻盈如母亲近七十年的身体
三个孩子追逐嬉戏,两个年轻的母亲
他们闹着,母亲跟着,慢慢迎来一场雪
一拨拨广场舞是最廉价的药
颈椎病、腰疼、食欲不振,还有一些疑难杂症扭扭就好
一道朝阳艳丽地照到广电大楼中央
她的美高于玫瑰
高于饺子的味道
白 纸
白纸黑字
那写错的符号
留给谁看
曾经错过的人
用涂改液能否找回
白纸上多难的诗行
没有仪式感
没有进入房间
那生锈的钥匙留给谁
一生中爱过的人
静静地躺在白纸上
选自《安徽作家》202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