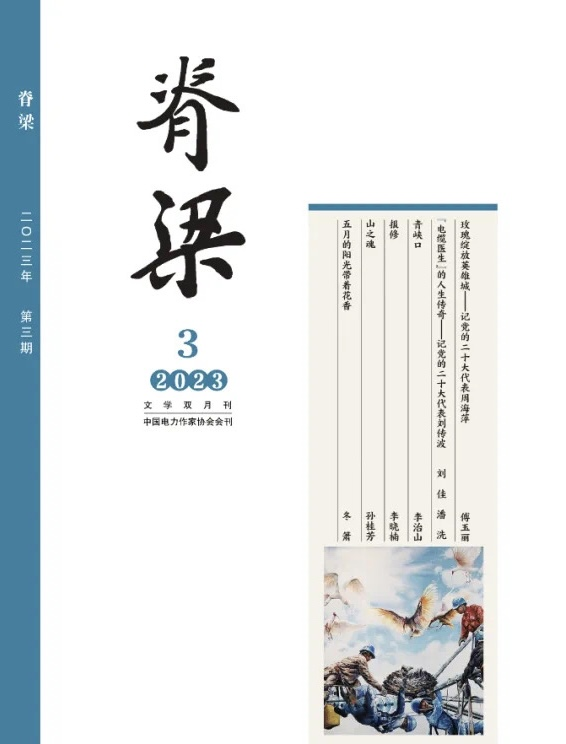一树梨花开(节选)
1
余天河站在走廊里,入目的是对面崖顶上的那棵野梨树,树上结满了花骨朵儿,已是四月头了,大别山里比山外低上好几度,欠了那么点火候,这花高低不开。耳旁一如既往是不停的水流声,潜水河从天河尖上流下,漫过崖顶,流进蓄水潭,冲刷水轮,落入崖底时发出的冲击声,丰水季呯呯嘭嘭,訇然如擂响鼓,枯水季沥沥喇喇,清脆如珠落玉盘,穿插其中的是机房里机器轰鸣声,嗡嗡嗡的,也不吵,主要是听习惯了,也已听了三年。今天星期四,再有三天就能交班了,余天河举头看了看天河尖上的朝阳,目光中透着焦虑,再看一眼那条山路,无奈地垂下眼帘,虽然心里揣着事,但却急不来,只能捱过这几天。那根本算不上一条山路,甚至根本就不能算是路,那是用凿子在圆滚滚的岩石上凿出来的石阶,勉强塞进三分之一的脚掌,借上力之前,脚掌得垫上几下,确定垫实了,才能使力,靠着这点摩擦力,一阶一阶的,慢慢登上圆不溜秋、滑不溜手的石崖陡壁。可每次上山,当脚踏上第一道石阶的时候,他脑子里就浮现出望山叔一瘸一拐的模样。早些年三道口水电站排班是三天一个班,自从李望山跌坏了腿以后,站里就改了规定,一个星期轮一班,并且在岩壁的边缘,从山顶到山脚,拉起一道镀锌钢绞线,用手攀拽,能借点力,也多了一道保障,让每次上山浑身就起鸡皮疙瘩的余天河心少了一些惊悸。一次县水利局领导到站里检查工作,看见李望山腿脚不便利,关心体恤他,让他不要到站里值班了,说换个人,老李拒绝了。后来余天河来了之后,听说了这事,有些想不通,问他当年为啥要拒绝,老李说,摔断腿是因为自己不小心,腿瘸了,慢一点就行,再说山里景色秀美,空旷静谧,不像城里嘈杂,整天乱哄哄的,这里是世外桃源,他喜欢这里,都干了半辈子了,舍不得离开。余天河不以为意,心道就算再喜欢,看了那么多年,也早看厌了,小的时候他跟他爹也上来过,上了山进了站,一呆就是七天,没人说话,那时电视还是个摆设,根本没有信号,他爹说,闷得厉害的时候,就冲着大山吼几嗓子,其余的时间就剩发呆了。现在好歹电视有了信号,接了班,遥控器就一直在手边上,只有那么几个台,轮番的看,广告也能看得津津有味。这破工作唯一的好处就是,上一个星期班能休息七天,余天河实在找不到还能提起他兴趣的地方。
2
五年前余天河大专毕业,当他打好行囊,元气满满地正准备动身南下深圳的前一天,他爹余有志打电话来,“工作我给你找好了,你明天就回来。”“啥工作呀?”余天河一愣。“回来就知道了。”不待余天河再问,那头已挂断了电话。余天河是个孝顺孩子,只能乖乖回家。回到家进了门,余天河急不可待地问老爹:“爹,你给我找的啥工作。”余有志眉梢挑了挑,硬邦邦地道:“接我的班,去三道口电站值班。”“你不是还有两年退休吗,凭啥要我接班!我的工作我自己找,不用你操心。”余天河脖子也梗梗的,他一想到自己要在那深山高崖之上待一辈子,就感到头皮发麻,全身起鸡皮疙瘩。“呸,自己找?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读书的时候光知道玩,就你那学历,能找着啥工作。”“爹,这年头,只要自己努力,哪都能挣到钱,你没听人说,北上广深那些城市,从打工仔到打工皇帝,拿年薪百万的多了去了。他们能,我凭啥不能。”“知子莫若父,你个瓜蛋什么德行我能不知道,从小贪玩,学习偷懒,说你你不听,你能吃得了那个苦!趁早死了那条心。”“爹,这事你说了不算,你不能把我箍在那深山沟里,你这不是帮我,你这是毁我。”说完,余天河背起行囊,扭头离家而去,奔向他向往的天地、美好的城市、自由的生活。然而现实与梦想的距离永远大于想象,一个初涉世事、意气风发年轻的心在现实面前遭遇了挫败。刚到深圳没多久,就因为水土不服,生了一场大病,治病花光了身上的钱,一想到他爹说的那番话,他赌气般地咬着牙没给家里打电话,找同学借了一点钱,然后凭着年轻硬抗,拖着虚弱的身体,出门应聘找工作。找来找去,因为学历偏低,又无一技之长,只能进工厂,每月基础工资两千元左右,多劳多得,可想多拿钱就得多加班,一天得干十二个小时以上,一个月拼死拼活也就能挣个五六千块,可这里的消费高得吓人,厂里不提供住宿,四五个人合租一套房,摊到人头也得六七百块,加上水电费,就去掉小一千,房间里什么味都有,成天还乱糟糟的,没有安静的时候,人也休息不好。厂里只供中餐,早晚餐自己解决,在厂里穿工装,出门穿的都是地摊货,其它的交通费、手机费、日用品等等,一个月到头能留个千八百的就算省的了。可碰上行业不景气就面临着失业,意味着没收入,生活顿时陷入窘境,积蓄很快就没了,又得硬着头皮,游走在大大小小的劳务市场,找不到固定岗位时,扎过钢筋搬过货,擦过玻璃送过快递,啥活都干过。余天河到现在才明白,所谓的打工皇帝,除了极个别有着特殊际遇的,或者也有特别能吃苦和努力奋斗的,大多数都是电视编剧编造出来的南柯梦。苦捱了一年半,临近春节,余天河正犹豫着要不要打个电话回家,他娘王红秀打电话来了,说你爹生病了,医生说是冠心病,不能干重活,不能做剧烈运动,不然随时都会有危险。可你爹上山去电站要走那么多路,还要爬山,那不就是剧烈运动吗,所以我就劝他,退了吧,在家待着,可你爹就是不干,说站里没人接手,总不能让老李一个人值班,不能让村里人没电用。你回来看看你爹,劝劝他。余天河回到家,余有志扔下一句“回来了”就没再理他。直到初四这天,余天河突然听到屋外有争执的声音,赶忙出来,看见娘正拉着爹的手说:“别去了,你这发病呢,不要命了,你再去就得把命送在山上。”“你别瞎掺和,人家望山为了大伙能过个亮堂年,一个人在山上值班,你还要人家在上面待到什么时候,做人要将心比心。”余有志一手撑着那辆破得叮当响的摩托车,一手按着胸口,脸色有些难看。“不行,你要去,我就去局里找领导。”“你敢。”“我一个农村妇女,我有什么不敢。”王红秀犯起了倔脾气,跟丈夫顶起了牛,两人僵持起来。余有志扭过脸,看着儿子,疑惑地道:“你真的肯去?”“…嗯。”余天河第一次去三道口水电站值班,是他爹陪着去的,把他送到山脚下后,反复叮嘱,最后看着他的身影在山谷间跳跃,逐渐消失后,才骑车返回。等余天河气喘吁吁地拽着钢绞线登上山顶,进了电站的门,就听到“哎哟”一声,望山叔一脸稀奇地望着他,笑容揶揄,“啥时回来的?”“年前。”“哦,那就是回家过年啊,咋又上山了?”“爹不舒服,我替他几天。”“不错,孝顺娃。还出去不?”“去,得挣钱啊!”“吔,那还不是一样。”“什么一样?”余天河不明白他话里的意思。李望山摇了摇头,背着手一瘸一拐地进了值班室。余天河跟着进来,李望山递给他一个旧手机,内存很小,网速很慢,基本只有打电话的功能。“这是值班电话,设备出故障,这边无法单独处理,或者山上断粮断油,再不就是紧急情况,比如像雷暴大风暴雨这样的天灾,你就打电话,没事就在山上待几天,等我来接班。”余天河接过手机,嗯了一声。“那我回去了,走之前到我家去吃顿饭,年前怀玉还问过一次。”余天河没啃声。怀玉是李望山的女儿,和余天河初高中同学,名字带玉,却是一块有瑕的玉,她左手天生六指,小的时候倒是没有什么影响,可上了小学以后,周围就有闲言碎语,说长六指的人天生命运多舛,生活艰辛,一般人沾惹了会不吉利,所以在学校里很少愿意和她做朋友,她在班上也很少说话,不大与人交流,默默地躲在教室的一角,无声地成长。倒是因为父辈的关系自小与余天河一起嬉戏,一起长大,上了初中以后,学校有人拿李怀玉的六指讥讽嘲弄她,说她是怪物异类,余天河为此替她出头打了几场架,惹得一帮顽劣少年阴阳怪气地起哄说他喜欢李怀玉,喜欢个怪物,从那以后,余天河就很少再和她说话了。高考以后听说她考了个不错的本科,之后就没再听到她的消息,算算时间,去年也应该毕业了。
第一次值班那几天余天河把大把的时间都放在发呆上了,对着天河尖,对着奔流的潜水河,对着静静的梨花沟。天空很蓝,阳光很柔,山谷很静,渺无人踪,心际空旷,适宜沉思,不必奔波,不必忙碌,不必焦虑,世界仿佛忘记了自己,或者此刻他并不属于这世界。
第三天临近午时,山坡下来了一个人,远远看见人影,余天河一愣,暗道,这是谁,看模样还是个女的,穿着一件白色羽绒服,手里拎着个不锈钢保温桶,等人登到石梯一半处,微微扬起了脸,余天河马上认出了她,虽然已经好几年未见。
“你上来干什么?”人还没到面前,他先没头没脑地来了一句。
“我爹说你替余叔值班,怕你烧不来菜,让我炒几个菜送上来。”李怀玉气喘吁吁地道。
“我娘给我带了。”“这不算着你快吃完了吗。”李怀玉将保温桶里的菜拿出来,放在桌上,“来,趁热吃,吃不完的放冰箱里,回头自己热着吃。”
“嗯。”
“听说你在深圳打工,赚了很多钱吧!”“没…没有。”余天河低下了头。
“嗬嗬,在那样的大城市里,只要自己够努力,一定能挣到钱。”
“嗯。”头垂得更低了。
“过完初八就得走吧?”“还没定。”“这几天在山上过得习惯不?”“还行。”余天河随口答道。
李怀玉一屁股坐在台阶上,丝毫没着急下山的意思,她面对天河尖,看着从上而下流淌的潜水河,呢喃地道:“你知道为啥这梨花沟里没有梨树吗?”
“我爹说当年为了建水电站,那半山的梨树挡住了进山的路,材料设备运不上来,村里人就把树都给砍了,造成现在梨花沟里无梨花的现象。”
“是啊,当时修这座水电站,梨花沟周边的乡亲们可谓倾尽全力,我爷爷和你爷爷,李塘和莲花两个大队的书记,带着村民们一起,在这湿滑陡峭的崖壁之上,深涧幽谷之中,唱着号子,开山炸石,修筑拦水坝,刀砍斧凿,凿出这笔陡的天梯,靠肩挑背扛,将机组设备送上三道口,才有了这水电站,是它点亮了梨花沟的第一盞白炽灯,带动第一台碾米机、榨油机、抽水泵,它给梨花沟带来了光明,带来了希望。”
她侧着脸,冲他盈盈一笑。余天河瞅着她的笑脸,光洁如玉,泛着柔光,他心底突地有一种感觉,原来她那么好看,以前可没觉得。
“跟我说这些干嘛!”
“是让你了解了解三道口水电站的来历。”
“有什么用,”余天河环视了一眼小小的电站,“三天两头的停电,有的时候灯好像鬼火,都没有煤油灯亮,各家的煤油从来就没断过,那些茶叶作坊,家家还得备个柴油发电机。”
“有电才有希望,碾米机、制茶机、榨油机、水泵等各种机器才能转得起来,没有电,不就回到刀耕火种的时代去了嘛,日子不就越过越退步了嘛!你从大城市回来的,现代文明怎么可能离得开电。”
余天河顿时语塞,悻悻地道:“跟我有什么关系。”
“没说和你有关系,这不是你代你爹来值班吗,跟你聊聊这电站。你知不知道,这里还有一样古董呢。”李怀玉话锋一转。
“古董?水电站里能有啥古董。”
“走,带你去开开眼界。”
两人来到后面的仓库,仓库的角落里有个木柜,上面积着一层灰,柜门也破了,没有锁,虚掩着。
李怀玉拉开下层的柜门,“看,过了这么久,也算是古董了。”
余天河仔细一看,原来是台小型发电机,他伸手拂去铭牌上厚厚的灰尘,却见铭牌上冲印的文字都是外文。
“你知道我英语不好,还让我看这个。”余天河脸色一囧。
“这不是英语,是德语。这就是三道口水电站的第一台水力发电机,是从奥地利进口的,是你爷爷和我爷爷两个大队书记去县里找了县长,经过县里市里特批,县财政局专门拨了外汇,才从国外进口来的,虽然只有18个千瓦,可金贵着呢。”
余天河忍不住伸手去摸了摸这个已经漆面斑驳、透着陈旧、曾经漂洋过海的舶来品,那外壳尘封下的都是久远的故事。
“我爹说,那时每天只在18点到22点之间供电,就这样,两个大队有一半的社员还用不上电呢。后来三道口水电站经过两次扩建改造,现在两台160千瓦的机组也只勉强够用,可见这几年村里用电增长速度得有多快。”
“你毕业了吧!准备干点啥?”回到了值班室,余天河随口问道。
“我参加了去年咱省‘三支一扶’的招募选拔,被录取了,县里把我分到了咱村,做扶贫工作。”
“任务重不重,困难应该挺多吧。”
“说重也不重,说难也不难,只要找对了方向,解决问题就行。现在梨花沟最大的问题依然在用电上,瞧瞧咱们隔壁的红山县,前年国家电网对他们实施收编,纳入大电网供电,再对原先水电供区电网进行升级改造,红山县仅仅用了三年不到的时间,就完成了脱贫摘帽。”
“你该不是我爹请来的说客吧。”余天河脑子里突然灵光一闪,质疑地盯着李怀玉道。
“咯咯咯,你才反应过来,不过不是你爹,是我爹,”随即她正色道:“我爹说,你爹身子不好,不管你答不答应接他的班,都不能再让他值班了,我爹已经向县局反应了情况,领导说正在物色人选。怎么样,有没有兴趣留下来?”
余天河紧锁眉头地道:“我考虑考虑。”
“行,你考虑考虑,我下山了,值完班去我家吃顿饭,再告诉我准信。”李怀玉摆了摆手,然后拽着崖壁里的钢绞线,顺着石阶下山,那渐渐远去的白色背影,像春风中绽放的一朵梨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