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4-04-01 来源:安徽作家网 作者:安徽作家网
近期,我省作家江飞散文《水上的传奇》发表于《人民文学》2023年第1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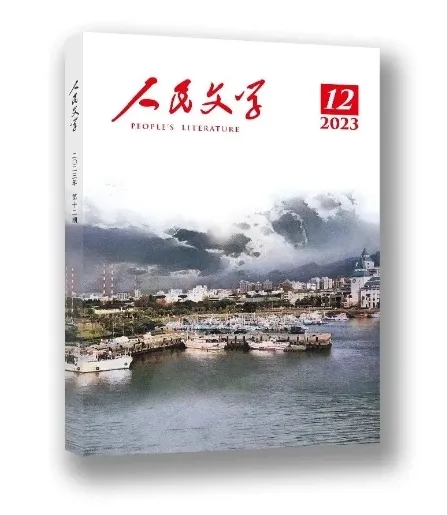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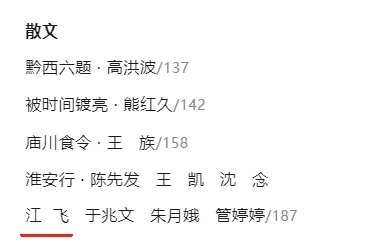
作品欣赏
水上的传奇
江飞
“这个古镇繁华了两千年,吴王夫差开凿邗沟时它就有了。如今是朝廷盐运史的驻地,官衙森然,店铺林立。大汉朝淮阴侯韩信和《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都出生在这里。小波罗上岸溜达了一圈,在船上他就闻到了茶馓的香味。茶馓是当地的特产,手工把面拉扯成细细的一线,一圈圈绕成巴掌大的一块,下锅油炸,金黄酥脆地出锅,舌头用点力,入口即化。”二〇二三年九月十七日,当我坐在淮安古城河下古镇的“文楼”里把一块茶馓放进嘴中的时候,不禁想起小说《北上》里写的这段话来——全长一千七百九十七公里、贯穿两千五百年历史的大运河则是他的文学原乡。一路北上的意大利人小波罗是幸运的,因为他见识到漕运时代最后的繁华,而我却只能面对历史的遗迹和亦真亦幻的历史,或许最繁华的历史也终究敌不过一块最日常的入口即化的茶馓。
历史是一条长长的大运河,千帆竞发,百舸争流;大运河是一条长长的历史,古往今来,绵延不绝。而淮安,正是一座漂浮在水上的城市,北有古淮河,西南有洪泽湖,东南有白马湖,它因运河而生,因运河而兴,它创造了历史的丰碑,水上的传奇。
传奇始于漕运,漕运是中华民族行走水上的智慧与故事。在春秋战国、秦汉、南北朝的刀光剑影中,漕运成为军事的后勤保障,成就了秦皇汉武的伟大功业。历史的意味深长在于,骄奢淫逸的隋炀帝却是大运河时代的开创者,他开凿的大运河,纵向沟通海河、淮河、黄河、长江与钱塘江五大水系,为盛唐文宋的清明上河、西湖歌舞提供了最好的注解。三千里京杭大运河,推动和刺激了中国传统的商业经济,担负起一个国家的生命线,更成就了长安、洛阳、开封、苏州、杭州、扬州、淮安等运河都市的繁荣。明清之际,地处运河中段的淮安更是因为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而成为漕运之咽喉,作为中央政府的河道治理中心、漕运指挥中心、漕粮转输中心和税收中心驻节有漕运总督和河道总督,得“天下九督,淮居其二”之名。“南船北马,九省通衢”,无论是南粮北调、北盐南运,还是丝、帛、茶、瓷、药材、手工业品等商品南北交流,作为南北分界的淮安,成为南北水运枢纽、漕运盐运集散地,成为“天下粮仓”。“襟吴带楚客多游,壮丽东南第一州”,这是何等的壮丽,这又是何等的荣耀!
万历七年移建在此的“总督漕运部院”的门楼依旧巍峨耸立,两旁的石狮依旧静默不语——它们是见过大世面的:漕督曾掌七省漕政,节万余漕船,数十万漕军,门庭若市的景象,犹如运河之上千万艘粮船“衔尾而至山阳”。尽管“帆樯衔尾,绵延数里”的盛况已难得再见,但如今在淮阴船闸等候的货船依旧络绎不绝,也依旧像往昔那样首尾相衔,有序通行。不同的是,曾经通闸需要等待几天几夜甚至十天半月,而现在只需几个小时,甚至更短。相较于快捷的陆运,水运的特点也显而易见,比如运量大、能耗小、污染轻、占地少、成本低、投资省。立于“京杭运河”号的船首,迎着烈日和微煦风,从淮安大桥下穿过,大大小小装满木材、沙石、钢材等货物的船舶,承载着千家万户的生活和希望,在两侧徐徐前行。“一闸不通,万船难行”,我遥望着淮阴船闸入闸口的闸门缓缓闭合,水位缓缓抬升,紧接着出闸口的闸门缓缓打开,一切都是那么井然有序、自然而然。在淮安港务中心的调度室,“船闸集中控制系统”正进行着实时监控,原来这“井然有序、自然而然”靠的不是听天由命,而是现代化的科学调度。
夕阳如金,水波不兴。我根本无法想象曾经的清江闸,如何“断缆沉舟”,又如何九死一生。那些幸存的人们,必须得感谢被誉为“中国大运河河工历史博物馆”的清口枢纽水利工程。历史上的清口枢纽是黄河、淮河、大运河三条河流的交汇之处,因为黄河夺淮、淮河水系被破坏,明代著名水利工程专家潘季驯采取筑堤束水、以水攻沙、蓄清刷黄、济运保漕等方法,在清口枢纽建筑了水流利制导、调节、分水、平水、水文观测、防洪排涝等大型工程,充分体现了人类农业文明时期东方水利水运工程技术的最高水平,代表了中国古代治河思想和科技精神的巅峰。“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从大禹治水到都江堰到清口枢纽,中国人的水上智慧和传奇技艺怎能不让我惊叹?
水波荡漾,夜色迷离。泛舟清江浦上,岸上人来人往,水上一座桥又一座桥。“夜火连淮水,春风满客船”,这风景,王侯将相、显宦世家曾见过,巨商富贾、文人墨客亦曾见过。遥望九层高耸的国师塔,庄严肃穆,灯光璀璨,如航标,映照浦上;御码头、石码头,如面孔,如灯火,如繁花,一闪而过。光绪二十七年,公元一九〇一年,清廷正式颁布停漕改折的令。“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吴山点点愁。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白居易《长相思》)相思一曲终了,漕运一令终结。大运河依然流淌,从不停歇,淮安却渐渐隐入历史的烟尘。
清江浦畔,花街烟尘未绝。花街上并没有花,只有高大的梧桐,在暗夜里默默守望。花街明清时就有了,很繁华,以前很长,现在只有这一小段。“虚窗暗透风如剪,深院絮飞雾似帘”,花一般的邱心如,二百年前也曾在这花街笔下生花,写就长篇弹词《笔生花》。此刻,这短短的、窄窄的花街上,只有三三两两的行人,和自由流动的手鼓与吉他轻柔的乐音。那是“花街微书局”门前,一支三五人的乐队,抱着吉他的女歌手正在浅吟低唱。高悬的“淮安清江浦”红灯笼下,是大大的“淮安”和“趁着青春年少,抓紧时间拍照”的黑底白字,显出一派时髦又本土的文艺范。忍不住驻足倾听,莫名就有些感动,为这群年轻的音乐人和自己一去不复返的青春。书局的老板是个面貌憨厚的“九〇后”,姓于,带我们去街头的一家“璞园糖水”。一碗色香味恰到好处的“木瓜桃胶”下肚,瞬间酒气尽散,甜上心头。当年“南船北马舍舟登陆”的人们也大抵如此吧,一路北上,风尘仆仆,到这里停下匆匆的脚步,拐进花香四溢的花街,走进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里。“南船北马”,我细细咀嚼着的这四个字,正是那支乐队的名字,或许也是未来某部文学作品的名字,但首先是一代又一代为生活而奔忙的中国人的代名词吧。
身膺民社寄,民以食为天。南船北马的人们,总会在运河河畔的酒肆茶楼交换各路消息,又总会在淮扬菜的滋味里相遇或重逢。“清淮八十里,临流半酒家”,全鳝席、全羊席、全鱼席,和精清新的淮扬菜系,伴随着漕运的兴衰,走过豪奢化、贵族化,最终回归乡土化、文人化。历史也好,个人也好,菜系也好,终究要走一条返璞归真、守常乐道之路。”犓牛之腴,菜以笋蒲。肥狗之和,冒以山肤。楚苗之食,安胡之飰,抟之不解,一啜而散。于是使伊尹煎熬,易牙调和。熊蹯之臑,芍药之酱。薄耆之炙,鲜鲤之鱠。秋黄之苏,白露之茹。兰英之酒,酌以涤口。山梁之餐,豢豹之胎。小飰大歠,如汤沃雪。此亦天下之至美也”。(《七发》)。作为淮阴人的汉代辞赋家枚乘,恐怕也难以抵挡笋蒲的魅惑,当然,他意不在此,而是以音乐、饮食等六件至乐之事,来劝诫贵族子弟不要过分沉溺于安逸享乐,而要学习探讨“要言妙道”,用道德调理自身。
我埋头吃着笋蒲,心里不由自主地想着“要言妙道”,想着想着,莫名就想起“中国淮扬菜文化博物馆”入口处的海报上是明日即将上演的京剧《安国夫人》。哦,原来除了尧帝、韩信、吴承恩、周恩来,抗金巾帼英雄梁红玉也生于此地!水上的传奇,不仅滋养了人们的口腹肉身,更孕育了一个又一个个传奇人物,并通过他们构建了中国的历史文化、道德伦理和“要言妙道”。一部波澜壮阔的运河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的传奇秘史啊!
杉青水秀,水流无声。游弋在高大笔直的两排池杉之间,犹如行进在历史和现实的夹缝之间,竹筏显得渺小,竹筏之上的人就更显得渺小了。撑筏的老船工是个异常健谈的人,姓崔,原是这片林场的员工,只听他一路妙语连珠,高声夸赞着“水上鱼米之乡”金湖。而我显得有点心不在焉,因为我更在意的是那水中不停晃动的光影,那天空与池杉的夹角,以及那小巧如菩萨、气度似万佛朝宗的气根。置身于金湖水上森林,仿佛来到一个世外王国,没有车水马龙,没有狗苟蝇营,今夕何夕,似乎已不重要。可惜,筏到桥头,又不得不匆匆离去,不经意转身瞥见一片开放的睡莲,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它们多么自在,多么幸福!
“水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这种角色,你不写作会忽略它。而一旦你把它视作一个审美对象,就会发现一条河可以带起你整个的生活。生活好像以一条河为中心,抓住了这条河就抓住了其他细枝末节的东西,或者说是纲举目张”。还是作家深谙“水”的意义。或许,所有伟大的时代都有一条与之相关的大江大河,所有平凡的生活和生命也都有一条与之相关的大江大河。时间顺流而下,生活逆水行舟,奔腾不息的历史与河流,一定会创造新的时代,新的生活,新的传奇……
作者简介

江飞,男,1981年生,安徽桐城人,安庆师范大学美学与文艺评论研究中心主任、人文学院教授,硕士导师。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复旦大学访问学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安徽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安徽省写作学会副会长,“江淮文化名家”领军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