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2-11-28 来源:安徽作家网 作者:安徽作家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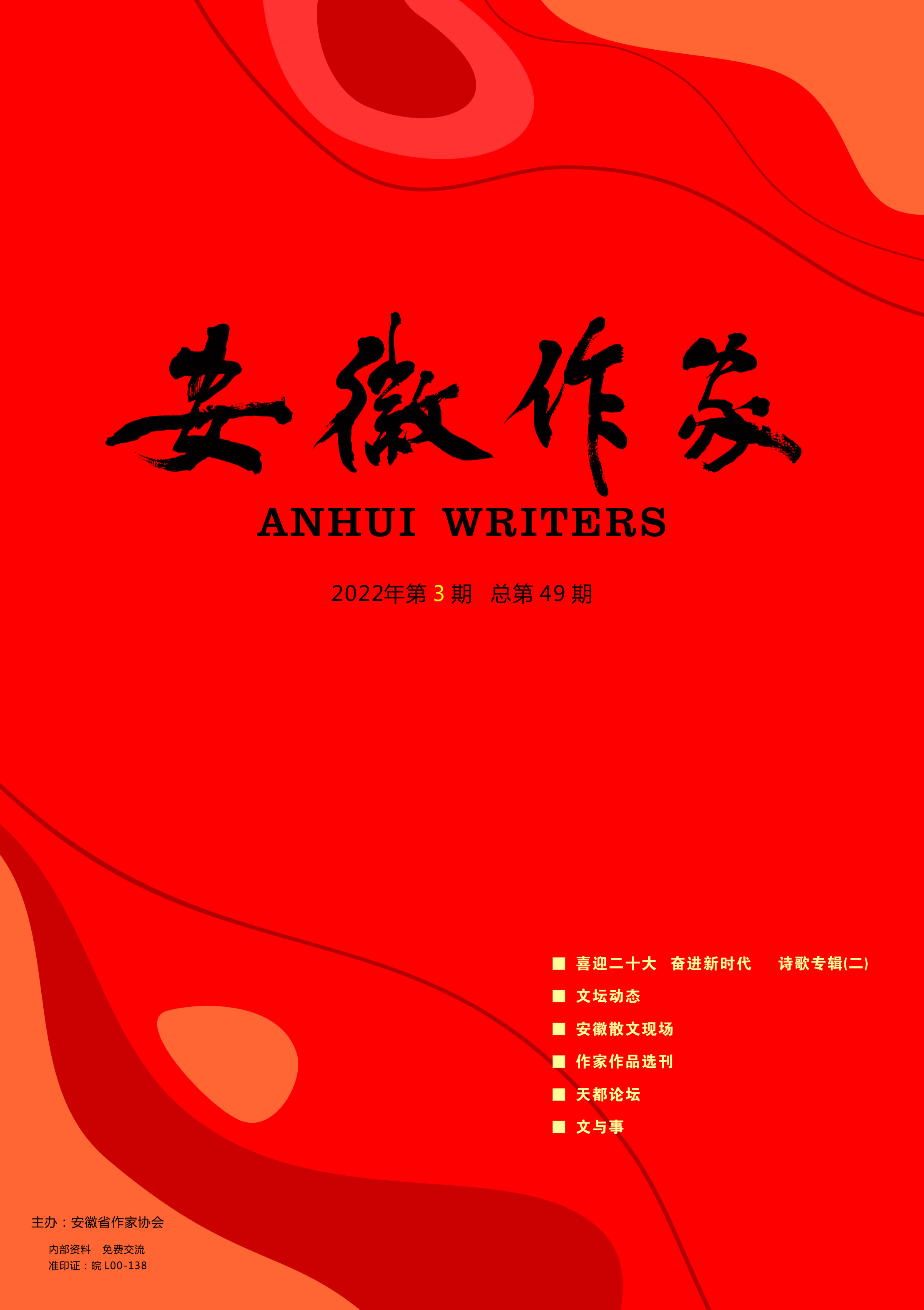
作品欣赏
散文观:作为一种见情见性的文体,散文对写作者的消耗太大了,大体量的写作势必会导致质量上的平庸。修辞立其诚。散文写作尤其需要“诚”。比较而言,我更喜欢有生命体验的散文,读这样的散文,能触摸到作者的呼吸、心跳和体温。
草木本心
江少宾
我是到合肥之后,才认识广玉兰的。阜阳路上,长长的两排,椭圆形的叶子肥而厚,正面光滑,反面粗糙,无锯齿,像一把把临风轻摇的小蒲扇。我在乡村长大,蒲扇太熟悉了,盛夏的傍晚,梧桐树下,一张咿咿呀呀的小竹床。破旧的蒲扇握在母亲的手里,朦胧间,蒲扇在我身上“噗嗒”一声,又在妹妹身上“噗嗒”一声。“轻罗小扇扑流萤”,母亲扑的不是流萤,是蚊虫。在牌楼,竹床不叫竹床,叫“凉床”。这个词是谁发明的?不知道,太准确了!睡到半夜,浑身凉洇洇的,疏朗的星光从梧叶间漏下来,像一滩流泻的乳汁在四周摇晃。星空是一方幽蓝的池塘,在瓦屋顶上倾覆,星汉灿烂,若出其里,看上去就在巢山之巅。离开牌楼许多年之后,我在江西的怀玉山、石台的牯牛降撞见过童年的星空——低矮的穹庐浮着一层毛玻璃,满天繁星就在毛玻璃后面,伸手可摘的样子。“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银河是一条幽蓝色的游动的光带,水晶一样,就快涨破了。好像已经涨破了。我久久地仰望童年的星空,竟无语凝噎,像面对一个阔别多年的亲人……我时常遥想童年的星空,也时常遥想母亲的蒲扇。
广玉兰开花有早有迟,在同一棵树上,能看到花开的各种形态。有碧绿如洗的花苞,如婴儿的脸,柔嫩可爱;有完全绽开的,花朵洁白而甜美,纺锤形的花蕊长约一寸。广玉兰香味淡雅,花期也不长,花瓣凋落之后,花蕊依旧挺立在枝头,已经长成了一根两寸长的圆茎。圆茎四周,缀满了紫红色的小颗粒,那是广玉兰赖以孕育新生命的种子。这时候的广玉兰不再是一棵树,而是黄昏里瞌睡的老祖母——风风雨雨都过去了,如今四世同堂,她在余晖里享受着岁月安详。
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飘萍于江湖,寄情于草木,中国自古就有歌咏草木的传统,但玉兰入诗却极少,一直到明朝,才偶现几首脱俗的玉兰诗,其中名气最大也写出了一点新意的,是文徵明的这首《咏玉兰》:
绰约新妆玉有辉,素娥千队雪成围。
我知姑射真仙子,天遗霓裳试羽衣。
影落空阶初月冷,香生别院晚风微。
玉环飞燕原相敌,笑比江梅不恨肥。
新开的玉兰花洁白优雅,仿佛绰约多姿的女子,她刚刚妆过的面容散发出美玉一般的辉光。远看时,满树的花朵像无数穿着素衣的美人,又像雪花一样轻盈起舞,真是美不胜收啊……文徵明写的其实是白玉兰。白玉兰和广玉兰同属木兰科,白玉兰是落叶乔木,广玉兰是常绿乔木。白玉兰先开花,后长叶,广玉兰花叶同放。另一个明显的区别是花期:白玉兰的花期在每年的二三月份,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诗句“影落空阶初月冷”可为佐证;广玉兰的花期则在初夏时节,大江南北,物候上略有差异。五月,天鹅湖南岸绿轴公园里的广玉兰就开花了,而六月份在北京,一株雨后的广玉兰刚刚绽开五六朵花苞,孤零零地站在一条幽深的巷道里,前后左右,全是槐树。槐树开花也是暮春初夏,但北京六月的槐花,枝叶间的花苞才刚刚绽开。我见过槐花怒放的繁盛景象:一棵槐树,就是一片花的海洋。一串串乳白色的风铃垂在枝头,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完全绽开的,像一只只展翅欲飞的白蝴蝶;有的还是花苞,像一盏盏小灯笼;有的只开了一半,宛若情窦初开的少女的脸……槐花样子淡雅,气味却迷人。
槐花可食(许多花都可食),且吃法很多,仅我吃过的,就有槐花鸡蛋汤,干虾蒸槐花,槐花蒸蛋,槐花炒蛋,槐花煎饼,槐花饺子,槐花面疙瘩,还有母亲最拿手的槐花饭。割晚稻的时候,母亲喜欢煮槐花饭,那是一个农家主妇能给予孩子的最高犒赏。母亲把槐花摘下来,在井边淘洗,然后一片片地铺在筛箩上,晒。槐花不吸水,晒两个日头就干了。母亲把晒干的槐花捧进一只褐色的铁皮筒里,挂在厨房里的一根横梁上。每一次煮槐花饭,母亲都要将右手窝起来,慢慢地探进铁皮筒,啄两小把槐花,放在米里,搅匀了,盖好锅盖,再弯腰点燃锅洞里的柴火。从田畈里归来,我们老远就闻到了槐花的香气,山芋的香气。锅洞里的草灰将熄时,母亲总要在草灰里埋一根山芋,等草灰冷成一堆死寂的灰烬,山芋也煨熟了。揭开一层焦烫的皮,山芋黄灿灿的,甜丝丝的,沁人心脾。母亲做的槐花饭有些涩嘴,却包着一缕淡淡的槐花香,没有一种滋味可以形容它。或许,那就是农家的味道,母亲的味道吧。
离开牌楼之后,我再没有吃过母亲的槐花饭。每一次想吃槐花饭,我首先想到的,总是母亲窝着右手,从铁皮筒里啄槐花的样子。母亲过世后,我已经没有了再吃槐花饭的想法。
合肥环城公园里有一大片槐林。五月,槐花开了,环城路上浮动着清甜而软糯的槐花香。那时候单位还没有搬迁,闲暇的午后,我时常在环城公园的甬道上散步。甬道上槐花纷披,浓荫深处,合抱着一对对你侬我侬的小情侣。我从不去惊扰他们。我也在五月的环城公园里谈过恋爱,那一树树槐花,也只有爱情可堪比拟,也只有两心相悦才不算辜负。密密匝匝的槐花下面,蜜蜂飞来飞去,嗡嗡,嗡嗡嗡。我嫌闹,却不嫌吵,和人类相比,蜜蜂更有资格享受这场盛宴。更何况,蜜蜂闹来闹去,最终都为人类做了嫁衣。父亲酷嗜槐花蜜,早一杯,晚一杯,温水冲服,常年如此。我喝过几次,相当失望,槐花蜜里,并没有那种清甜而软糯的槐花的香气。
若以花喻人,清甜而软糯的槐花,当是情窦初开的少女,白居易诗云:“夜雨槐花落,微凉卧北轩。”无论是开在枝头,还是零落在地,槐花的气质都是少女的;而晶莹皎洁的玉兰,无疑是热情洋溢的少妇,明人张羽的诗:“芳草碧萋萋,思君漓水西。盈盈叶上露,似欲向人啼。”樱花也有一种慵懒的少妇美。中国科技大学黄山路的校园里有一条“樱花大道”,在微信朋友圈里著名着,近在咫尺,我却一次也没有去过。武汉大学也有一条著名的“樱花大道”,友人多次邀约,我也从未允诺。咏樱花的诗词不多,好的更少,我只记得一句,苏曼殊的,“芒鞋铁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玉兰和樱花都太奔放了,我不喜。诗人好像也不喜。少妇一旦奔放起来,往往了无诗意。
桂花是花中的美少女。桂花,又名木樨,花簇生,果实紫黑色,俗称桂子。现知的桂花品种至少有一百多个,常分为四大类:黄色的金桂,味淡香;白色的银桂,香味浓;红色的丹桂,香味较淡;最常见的是四季桂,俗称月桂,花期较长,但味道很淡。桂花是合肥市的市花,几乎遍及大街小巷,寿春路、黄山路,大蜀山,植物园,包河、逍遥津、琥珀潭、环城公园……八月桂花遍地开,满城暗香浮动,连发梢上都染上了桂花的香气,如丝如缕,心旷神怡。白居易诗云:“遥知天上桂花孤,试问嫦娥更要无?月宫幸有闲田地,何不中央种两株。”咏桂的诗词不胜枚举,佳句也不少,或许是桂花迷人的香气,激发了诗人不羁的想象力。据《晋书》载:晋武帝年间,郄诜出任雍州刺史,晋武帝请他自我评价,郄诜毫不谦虚地说:“我就像月宫里的一段桂枝,昆仑山上的一块宝玉……”面对狂傲的郄诜,晋武帝不仅不以为忤,反而大笑着予以嘉许。后人便用月宫中的一段桂枝、昆仑山上的一块宝玉来形容特别出众的人才,这便是“蟾宫摘桂”的由来。蟾宫就是月宫,吴刚月宫伐桂的故事,在中国民间流传甚广,妇孺皆知。桂花和月,也成为秋赋的核心意象之一。唐朝以后,科举制度盛行,蟾宫摘桂便成了科举及第的代名词。蟾宫,摘桂,一静,一动,想想就很美啊!激动人心。
每次看到桂花,我总会无端地想到丰腴的大唐。少女般明媚的桂花,也配得上那个丰腴的大唐。大唐的桂花开在巍峨的庙堂里,开在李白王维白居易的诗歌里,开在唐玄宗美轮美奂的《霓裳羽衣曲》里。中国栽培桂花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春秋战国时期的《山海经》、屈原的《酒歌》、东汉袁康等辑录的《越绝书》、西汉司马相如的《上林赋》,以及晋人嵇含所著的《南方草木状》中,都写到了桂花。在民间,桂花的广泛栽培始于宋,盛于明。桂花枝繁叶茂,无论是开花还是散叶,都是一团和气,多子多福的样子,有一种东方女性的美。胡兰成说,桃花,难画,因为要画得它静。桃花太艳了,近乎妖,静不静我不知道,霜降之后的迟桂花倒是静的。花坛边,夜露垂降,天地寂然,桂花兀自扑簌簌,一朵,两朵,三四朵。落叶总是悲秋,但桂花落,看上去既娴静,又美好,心底仿佛有清风徐徐拂过。“人闲桂花落”,少时读王维,这一句总是念念不忘,每次读,都像一个人潜回故乡。
“月宫赐桂子,奖赏善人家。福高满树碧,寿高满树花。采花酿桂酒,先送爹和妈。吴刚助善者,降灾奸诈滑。”桂花酒是人间佳酿。中秋饮桂花酒的习俗在我国各地流布甚广,屈原的《酒歌》中已有“援骥斗兮酌桂浆”、“奠桂兮椒浆”的诗句,可见饮桂花酒的年代已经相当久远了。
除了酿酒,桂花还是一种天然药材。桂花性温味辛,具有健胃、化痰、生津、散痰、平肝的作用,能治痰多咳嗽、肠风血痢、牙痛口臭、食欲不振、经闭腹痛。由桂花蒸馏而得的“桂花露”,具有舒肝理气、醒脾开胃的功效,能治口臭、咽干等病,是上等的饮料。桂枝、桂子、桂根皆可入药,由桂枝、芍药、生姜、大枣、甘草配制的桂枝汤,专治外感风邪、肾虚等症。桂根可治疗筋骨疼痛、风湿麻木等病症。桂花晾干后可以冲茶。某年,在皖南祁门某个古村落的水口,我遇到一位自产自销桂花茶的老农,他家的后院长着两棵桂花树,两棵都有一百多年了,接近三层楼高,树冠如盖,树干需要两个人合抱。老农自己说,他做桂花茶已经二十多年了,每年能做五六斤,自己喝的少,大部分用于销售。冲泡之后的桂花像饱绽的粥粒,贴近杯口,淡黄色的茶汤里,漾起一股扑鼻的桂花香。老农的桂花茶半斤起售,六百元,太贵了,我只好泡了一杯,坐下来,续了三次水。临走,我在杯子底下压了五十块钱,老农没有拒绝,笑眯眯的,装着没有看见。那是我喝过的最贵的茶叶。
桂花糕。桂花蜜。桂花糖。桂花粥。桂花鸭。桂花糯米藕。桂花……桂花有各种各样的吃法,每一种,光看名字,就透着一股馥郁的香。还是白居易的诗:“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邵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2011年国庆,我陪父亲游杭州,西湖、岳王庙、灵隐寺、宋城都去了,最让我难忘的,还是朱利平凌来芳夫妇请我们吃的桂花山药。太好吃了,人间至美。饭店的名字我忘了,规模不大,门前有两株苍翠的香樟,高约两丈,一地浓荫。
老家的院子里也有一棵桂花树。小村牌楼,也只有这一棵桂花树。父亲喜欢栽树,梧桐,香樟,枫香,女贞,栾树,构树,海棠,枣树,桃树,杏树,香椿,刺槐,松树……破罡街上能买到的树苗,父亲都买回来栽过。现在的小村,已经没有人栽树了。春节,回来的人多,留守在家的老人会提前上山,砍几棵松树或枫香,晒干了,当柴火。巢山上的松树和枫香,已经长野了。它们在巢山上兀自生长,和老人们一样寂寞。
百般红紫斗芳菲。这是草木对大自然的回报,也是对人类的丰厚馈赠。遗憾的是,除了自幼熟悉的草木,在植物学方面,我长期停留在小学生的水平。面对合肥街头那些琳琅满目的花花草草,我曾经一片茫然,甚至不知道路边那种随处可见的矮灌木,就是大名鼎鼎的石楠,更不认识榉树、朴树、紫薇、黄连木、鹅掌楸、金边黄杨、杜英、无患子、五彩苏、吉祥草,甚至一度区别不了芙蓉和木槿……一个不关心草木荣枯的人,势必索然无味,他不会发自内心地热爱亲人、自然和社会,近乎面目可憎,几乎不足以谈人生(这当然是我的个人偏见,过于粗暴和武断,面目也很可憎)。人进中年,我越来越喜欢深居简出,生活随性而简单,逐渐疏离形形色色的圈子,基本不参与无谓的应酬。每月为数不多的几个休息日,我喜欢带孩子去野外踏青,教他背唐诗,读《诗经》,识鸟兽草木之名。在我看来,辨识草木的过程,就是重新认识自我的过程,就是自己给自己洗心洗肺的过程。自然中的每一棵植株,其实都是我们的故人。每一根花草,都是我们的血亲。草木有本心。自然中葳蕤的草木,附着有我们的情感、体温和灵魂。
我喜欢梧桐和桑树。梧桐是芜湖路的标志之一,这是一种父性的适于怀旧的树。秋天的黄昏,夕阳西下,梧叶斑驳,有一种沧桑和萧索的美。桑树是属于故乡的植物,有桑树的地方,总有炊烟升起。炊烟飘拂的屋顶下,总有我们的亲人,坐在锅洞旁边,温暖的火苗,舔红了大地一样苍老的脸。
我在合肥没有找到成林的桑,找到过几株伶仃的梓。古人栽桑是为了养蚕,种梓是为了点灯(梓树的种子外面,白色的就是蜡)。小时候,每到春天,菜园里,屋脚边,总会抽出一两棵幼苗,每次看见,我们总要除草一样将幼苗连根拔起。那时候我们都不认识梓,现在认识了,菜园早已荒废,老屋的院子里杂草丛生。没有了梓。屋顶上,炊烟不再升起。
都说“吾心安处是故乡”,吾心安处,不在合肥。岁月如白驹过隙。屈指算来,我在合肥,已经二十二年了。
(选自《安徽作家》,2022年第三期)
作者简介

江少宾,上世纪七十年代生于安徽枞阳,供职媒体,业余写散文。曾获人民文学奖、冰心散文奖、老舍散文奖、西部文学奖等。主要作品有散文集《回不去的故乡》《大地上的灯盏》。
作品欣赏
散文观:佛经讲,不要“法缚”。我写文章,不喜欢既成定例。随心随性,自然成文。
文章小道,但若能通于大道,就已非小道了。只要足够恳切真实,就能够以小见大。我是一,也是一切。是芥子,也是须弥。
被风吹绿的笔记本
文 河
年后立春。时值阴历正月初7。风细了,圆了,长了。丝丝吹着——穿过针眼儿,若有若无,仿佛来自灵魂的罅隙。阴历21号,上午,有阳光。阳光变暖时,便成了一种抚摸。在路边,我发现那株野海棠的枝条上爆出了芽粒。星星点点的。腥红。很红很红的颜色有尖锐感,像针尖。好些年了,它一直没有开花。不知道今年它会不会开。我看了一会,感到很愉悦。感到春天正一针一线的把我织进她的图案中去。
麦子还没起身儿——是那种待要起身,犹未起身的状态。但看上去明显比年前绿了。这是在双庙地界。双庙,一个地名。我曾在此生活过几年,因此,对我而言,它已经超越于地名。它是一枚灵魂的邮票。沿着黑茨河蜿蜒向南,在去神农药材厂的堤坝上,是一条杨树林带。从白龙桥到药材厂的这段距离,我看到了很多鸟巢。一个、两个、三个……一共十七个。鸟巢很大,粗糙,简陋。有乌鸦的,也有喜鹊的。这些鸟巢无一例外都搭建在最高的树梢上。有的一棵树上甚至有两个。很快,这些杨树就会长满叶子了,就能把鸟巢掩藏起来了,并且又慢慢把它们举向一个新的高度。这样,过不多久,鸟巢中就会孕育出幼鸟,林子里就会充满新的歌唱。从神农药材厂出来,在去王大庄的路上,我才看到五六只乌鸦,它们在杨树上飞落。我总感到乌鸦是种孤独的鸟儿。这么多鸟儿在一起,只不过加深了它们的孤独。又过一段路,在黑茨河滩上,我又看到十来只喜鹊,溜河风把它们黑白分明的羽毛吹得有点零乱。我在风中一动也不敢动。
在早晨,沉默整整一个冬天的花斑鸠突然叫了几声。是一只。在西沙河对岸那片杂树林子里。从此,在以后的许多个早晨它都会不停的叫下去的。我怀疑那片树林里还应该有一只斑鸠。只不过此时还没鸣叫。阳光明净。早晨的鲜明的阳光。古诗“初日照高林”,写的只是事实,但在一个经验主义的层面上,却有着一种超越日常性的质朴的美感。我身边的这棵野石榴树的枝条变得柔韧了,树皮吹弹得破,充满了一种生命的力度。去年,这棵树结了七个野石榴,小小的,圆润的红皮石榴,像北斗七星。毫无疑问,今年,它会结的更多。天空会在它披纷的枝杈间降下一个更为璀璨的星群。沉寂中又是一阵斑鸠叫。我没有到河对岸去。我在河这边停下来。我一直守着一条窄窄的理想主义的河岸。
从贾顾庄到西沙河之间的这条路,我不知道曾走过多少遍了。同一条路,走得越多,越证明我生活的单调。但是,反过来说,为什么我就不能通过对简单有限事物的反复描述,来使自己抵达某种繁富呢。从贾顾庄到西沙河之间的这条路,中间还隔着李营。李营西头的那片天空。去年夏末,下午,阳光白亮亮的,当我经过时,曾看到一大堆雪白的云。映着深邃渊静的蓝天,映着野地里那几棵绿叶郁郁的大桐树梢子,那白云显出极其强烈的亮度和雕塑感。当然,那片白云早就消失了——过不多久就消失了。缘起缘灭,云聚云散。如今,只剩下一片空旷的天空。只有我知道,那片天空,曾有过多么壮丽的景象。只有我,一直对那片白云念念不忘。因此,每次走过那条路时,也只有我一个人感觉到那片天空有一种无法言喻的荒凉。李营西有一大片樱桃林,小小的腥红色花骨朵刚刚从枝条上脱颖而出。脆弱的美从虚无深处再次来到人间。我一直在某种极端的有限性中生活。是的,我要把同一条路,反复走,经常走,只到把它走成一种无限,只到用尽自己的一生。
那所乡村诊所在秦小庄东边,靠着一条砂礓路。一个小小的院落。三间出檐瓦房,青色的砖,灰色的瓦,白色的院墙。它的瓦很好看,半圆弧的小筒瓦,积满青苔,是小土窑烧的。八十年代末期这种小土窑就淘汰了,因此,这样的瓦如今极少见了。现在的瓦都是红色的片瓦。一个小筒瓦就像一个半括号,这些半括号顺势叠彻,呈鱼鳞状,便有一种沉静典雅的韵律感。诊所有着古朴清凉的色彩,有着皖北平原特有的深厚滞重的宁静,也有着可以看得见甚至掬在手中的清幽幽的光阴。我喜欢这个诊所的名称:“一根针,一把草”。这个名称有着传统中医的平和、沉稳和自信。甚至略微显出了某种简洁的意味。院子里种着何首乌、桔梗、大青根、麦冬、白芍、忍冬(这种植物的花朵在福克纳的小说《喧哗与骚动》中有着那么浓郁暧昧的气味)。还有几种药草,我叫不上名字。根茎最大的那株何首乌被制成了盆景。白芍刚刚冒出红艳艳的芽粒。一只鸟儿在极高的天空中叫了一声,像一滴饱满的雨水,在一大片青荷叶般寂静的天空中滴溜溜的滚动好大一会儿,然后才突然笔直地落下来。生命在天地间流转着,并且波澜不惊。
在这片平原上,这些村庄其实大同小异。有些零乱和陈旧,像被一阵大风突然刮成这个样子的。并且永远陷入寂静之间。甚至在刮大风时,这些村庄也是寂静的。风把声音都刮跑了。冬天,这些小村庄就更寂静了。尤其是夜晚。寂静到极处,世上所有的声音倒仿佛又回到寂静之中了。这样,寂静反倒成了一种更大的声音。冬夜,一个小村庄就是住了再多的人,还是空,还是寂静,还是感到时空和岁月的无边无际。冬天的房间需要住上人,需要有灯光,熄灯后房檐上需要夜夜挂满古铜色的大月亮。风刮过来,刮过去,然后就刮到了春天。这时,风会把一些带走的东西送回来。风同时刮进所有空荡荡的房间,把色彩和温暖还给人间。风吹皱河水,吹皱女人的衣衫,还把一些人的心吹成涟漪。当然,风还吹动更多东西。慢慢的,村庄在风中发生变化。墙角的花朵在你看到或看不到的时候一夜之间就红了。然后,在你看到或看不到的时候,一夜之间,有的落了,有的变成了果实。星星特别大,特别亮,挂满酸枣树瘦瘦硬硬的枝条。春天到来的时候,我经常在村子与村子之间游走,直到盛夏来临,绿荫重新把我覆盖。村庄,一个最绿的词。记得二十年前的暮晚,父亲曾让我到邻村杨桥去找他的一个老同学喝酒。我很快就到了。整个村子静悄悄的,似乎空无一人。记得当时我曾想道:这整个村子的人都到哪里去了呢?这儿有种古朴、废弃和遗忘的气息。我感觉自己好像一下子来到另外一个极其遥远神秘的地方。村口有个大水塘,塘里堆着菱角叶子,开满金黄色的小花。也许还有莲藕。一株粗可搂抱的大黑皮柳树斜卧在水面上。到处是撕裂不开的浓荫,铺天盖地,似乎把我的双肩都压疼了。浓荫中还有许多幽暗又闪烁的光线、光斑和光点。那种寂静、温煦、厚实的氛围(就像一个梦境)包裹住我。我怀着好奇而又虔敬的心情放慢脚步……那时我才十来岁。我还没读到保罗·策兰的诗句:“每当我与桑树并肩缓缓穿过夏季,它最嫩的叶片尖叫”(王家新译)。那强烈到近乎尖锐的内心感受啊!那种感受我至今不忘,——但至今仍无法完全清晰的表达出来。
我是去年夏天发现那道沟渠的,它在三河村西南角。那是一个早晨。我先是从老远的地方看到那个四围长满杨树的水塘,然后就信步走过去。还没到那儿,就听到哗哗的流水声。那条沟渠从水塘向西沙河蜿蜒流去。刚下过一场暴雨,水积得很满。渠道两旁长满茂盛的荒草。几只鹌鹑突然窜上天空。我顺着流水没走多远就返回来,因为草叶上露水珠子太多,把裤脚都打湿了。深秋的一个黄昏,我又去过一次。渠水变得又细又浅,几乎看不到流动。夕阳一片火红。枯黄的茅草在西风中发出极长极硬的声音,细细的,不绝如缕,像针尖,一下下扎在心上。白色的花絮漫天飞舞。我静静站一会儿,走了。整个冬天,我一次也没去过。但我老是记着那个沟渠。有时我想,我应该再去看看它。但我最终没去。我第三次去的时候,已是春天。春天对我来说,更是一种信念。只有一无所有的人,才能看到更多的春天。这次,我顺着这条沟渠一直向前走。最细微的事物也能把我带走。我想,就算从这个水塘到西沙河这段短短的距离,也足够我走这一辈子的了。我走啊走啊,像个无助的孩子。
第一次看到这些石楠的时候,并不认识它们。后来,回去查了查资料,才知道它们的名字。以前,曾在勃朗特三姊妹(夏洛蒂,艾米莉,安妮)的小说中,读到过描写这种植物的文字。它们在哈代的小说中也大量出现。而这几丛石楠就长在刘关小学校园南面的空地上。厚墩墩的叶片呈暗绿色(它们的厚度很像枇杷叶,色泽稍浅,但叶形要比枇杷叶俊秀)。叶片层叠有致。很多长青树的叶片只有等到新叶长出后才会脱落,而石楠的叶片则能经受好几个冬天。现在是春天了,石楠的枝头又萌生出新的叶芽。这些小小的鲜嫩得不可碰触的叶片,阳光中闪闪发亮。当你凝视它们的时候,你会感到这个世界正在慢慢融化——融化成旋律、色彩、光芒。我早就想写一写这些石楠了。这最纯粹的生命。我看到一些事物,如果我不能把它们表达出来,我觉得这就是我对它们的亏欠。我必须浩大。我必须在死亡与永生中写下最动人的文字。
(选自《安徽作家》,2022年第三期)
作者简介

文河,生于上世纪70年代,太和县人。主要写作诗歌和散文。出版有散文集《清晴可喜》《城西之书》等。
作品欣赏
散文观:写作就是与日月星辰、大地山川、草木鸟兽、云雾苔石和古今人默默对话,与另一个隐藏的自己私语。其间情境,秘密又欢愉,孤寂又痛快。接续中国诗骚和文章传统,继续发现汉字之美,是我的使命,也是文章实践上的自觉。
旧年的丝瓜吊在木兰上
储劲松
洵 美
蓝草染的浇花布真是清美,当年外婆拿来包头,有青白颜色,也有清白家风。
葫芦、丝瓜、黄瓜、月亮菜、瓠子吊在豆棚瓜架上,静女其娈,洵美且异。
阒无人迹的山谷流泉好看。
农家女子壮硕的身板和黑檀似的肌肤,是妈妈年轻时的模样。
古民居的马头墙、鱼鳞瓦、瓦当、镇脊兽、天井、木雕人物,苔色苍苍的大青砖,逸笔草草的芝兰仙鹤图,墙上挂的草帽、蓑衣、竹篮子,是记忆里的故乡。
竹叶草洵美,板栗树洵美,玉米须洵美,水稻花洵美,在上面奔跑、追逐、求欢或者静伏的瓢虫洵美,甚至黑壳、黄壳、铜绿壳的金龟子也洵美且异。
流霞好看,腾雾好看,卿云好看。飞鸟好看,蚂蚁好看,潜翔水底的鱼虾好看。泥土好看,毛石头好看,松竹连它们在日月天光下的影子都萧然动人。
清晨的毛草和石菖蒲,叶片和叶尖上的凝露映射朝阳,其姿色与风情,可谓泠然,可谓清绝,美好得叫人无可如何。
钱锺书当年鄙视吴宓之为人,骂其无行,顺便牵连到他苦恋的毛彦文,用英文讽刺她是“年老色衰的风骚娘们”。其实这个风骚娘们年轻时是养眼的,即使老了,也有清气,乡语谓之“清丝丝的”。
天空之下,大地之上,一切原生之物,本质、天然、朴素、至美,没有不好看的。不好看的,往往是过度变异的人,迷失了天性本心的人,被欲念和利益禁锢的人。不好看的,是人发明制造出来的诸多反生命反自然的物事,譬如枪炮、塑料、地沟油和海洛因。
在大别山里,一个从前几乎是大荒之境而今依然存有古人遗风的小城,我活了很久。居住在青山之中,浣洗在绿水之畔,日日月月与草木鸟兽、白云苍狗、园蔬篱落为伍,感觉不到日月飞逝老之将至,以为这一具皮囊,可以与草木同春,与鸟兽同秋。
梅雨季初来的一天,一夜风雨大作之后,第二天望见满目夏花,石榴、荷花玉兰、女贞子、一年蓬的花,又望见满树膨大的果实,毛桃、五月桃、红梅和红叶李的果实。这些夏日习见的花果,我见过数十回了。从前见了,觉得好看而已,心里喜悦而已。那一天见了,忽然想到《知北游》,庄子在文章里说:“忽然而已”。天地自然不老,任他白驹过隙、黑驹过隙、枣红驹过隙。山川草木不老,由他冬春夏秋。人生易老,一回相见一回老,一生能见此情几遭,能见此景几回?
那一天,晨光明亮洒了一身,一念至此,眼前忽然就暗淡了一些。
生活仍然继续,貌似轰隆其实寂寂地继续。
在山野里,我以草木鸟兽为师,尽量遵从生物的本能和本性生活,衣但求暖,饭但求饱,住但求安,行但求稳,以为如此就好。安妥肉身之外,以书籍喂养精神,以文章抒发怀抱,以为文章载道,文章也载性。
我是说尽量,因为这种遵从很显然是不可能的。长安米贵,居大不易,活着并不容易,遵从本心活着更是痴心妄想。但写作的人,都是耽于妄想的人,所谓妄想,姑妄想之。也都有程度不同的痴心与痴气,像大观园里的香菱学诗艺。曹雪芹于这一节写得尤其细微:“香菱听了,喜的拿回诗来,又苦思一回作两句诗,又舍不得杜诗,又读两首。如此茶饭无心,坐卧不定。”
写作将近三十年,持续许多岁月而痴心不改,根子里,是有与时间抗衡的执念或者说妄想的。与时间抗衡,这显然更加不可能。岁月如驰,驰驰啊,“日驰驰焉而旬千里”。古今人的传世文章,浩浩洋洋,留在石头、兽骨、龟甲、竹木、绢绸、纸张中,锲刻在时间之上。转念一想,古今那些以文章为性命的人,痴痴复痴痴,有几人活过了百岁,又有几人文章传世?
但愿文章老厚,但愿肉身长葆草木精神,但愿年年写得几篇好文章。
草木温柔敦厚,朴素质直,一如上古的大人君子。《周易》《山海经》《诗经》《楚辞》《汉乐府》《古诗十九首》里,篇什草木华滋。自此而下,古今人的诗词曲赋和文章,一路草木蓊茂。风行草上,风行木上,时间的风吹过草木,吹过人世。草木不言,生来离离繁盛,枯后养息待发,生死荣悴等闲视之。与上古的大人君子相比,草木更符合《周易》之“易”的内涵:简易、变易和不易(不变)。
古人说,要多识草木鸟兽之名,又说,要多识前言往行。
久居山野,人在草木鸟兽间,草木鸟兽之名,我识得的万不及一。某一天我看见一只大鸟走路,像人一样迈开前后脚,左右左,一二一,又看见一只小鸟走路,它是双脚并立蹦跳着走的,一跳又一蹦。这两种鸟在大别山中寻常可见,我不识其名倒也罢了,当时还好奇它们走路的姿势竟然如此不同。后来一拍脑壳,哦,它们的脚有长有短。
至于前言往行,前代圣哲的言语行事,也与草木一样敦厚温柔、质直朴素,像先秦的诗歌一样,更是难以效仿和企及。
草木朴素,世道人心原本素朴。从孩提时起,就与青梅竹马的伙伴一起埋锅造饭:杜仲的叶子锤得像丝绸,拿来当菜;红芋的茎块用石片切一切,拿来当饭;折断蒿子的茎杆,拿来当筷子;松针搂一抱,拿来当柴。五六开裆童子,做饭吃饭装腔作势,吃得快活,耍得快活,像草木鸟兽一样快活。
后来渐渐长大,身条渐舒,喉咙渐粗,心渐大,渐渐不可收拾。渐渐不可收拾的,不仅是容颜,这旧日的好河山,还有心性,这与阴山岩画一样古老的本心。
热爱草木,景慕草木,亲近草木,是本心本性。我们的祖先以草木为衣,以草庐为屋,脚穿芒鞋手执木杖,都很闲,像草木鸟兽一样闲,像雨点、朝雾、夜星、流水一样闲,闲得夜夜天天思考来处和去处。我们都很忙,忙得忘记来处和去处,忘记自己本质上是一只动物。
愿心常常闲,愿文章常常有草木气,愿活着常常有草木心。
我也有一时苟且,我也有许多草木文章。
放 胆
日月星辰,这是天的纹理;山川原野,这是地的纹理;“素履之往,独行愿也”,这是心的纹理。天的纹理谓之天文,地的纹理谓之地理,心的纹理录于纸上谓之性情文章。
我有几卷性情文章,你有陈年老酒不?若有,何不学古人慷慨,“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
据说,有青楼鸨儿向苏东坡虔诚讨教写文章和饮酒的秘诀。
鸨儿问曰:“先生向不善饮,而以文名世,何以臻此,愿闻垂教。”
坡公稍稍沉吟,道:“文章无窍,唯率性耳;酒事无量,唯放胆矣!”
这段对答,是我从他人文章中拾来的,似乎不见于史乘和前人笔记。但书海泱泱、文山苍苍,这一典故或许就藏在哪一部我未曾读过的书里也未可知。即使是后人杜撰,也杜撰得好,很接近坡公的言语行事风格。
言行,君子之枢机;文章,心迹之表露。
一人有一人的言行,一人也有一人的文章。
近年时常温习坡公著作,越发以为东坡文章是天人之合,有仙狐鬼怪相帮衬。又时常读张岱,越发以为张宗子文章离经叛道超凡入圣,亦有神鬼暗中撮合。苏子《记承天寺夜游》《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超然台记》诸篇什,张子《湖心亭看雪》《扬州瘦马》《琅嬛福地记》诸作品,放胆直下,率性成文,令人翩跹欲舞讴哑欲歌,妙不可言。我愿效仿郑板桥和齐白石膜拜徐渭,文章以苏东坡和张宗子为师,甘作其门下走狗。
席上饮酒,古人以戎事作比,谓之“酒兵”,凶险之事也。放胆,就像霍去病率汉家轻骑出陇西横扫匈奴,夺其焉支、祁连二山,使其六畜不蕃息,令其妇女无颜色,非胸中有文韬武略又胆子极肥者不能。
率性,顺其本性,从其天然之性,于三岁童子容易,于尘垢蒙了身心的成人却难。这本性,原是天所赋之,在尘世里几番滚爬早已失去,想捡拾回来,得靠后天不懈地涵养、修为。如《周易·系辞上》所言:“成性存存,道义之门。”不断蕴存和涵养,以成全天性,让它存续不断,就找到了进入道和义的门户。
因之,率性和放胆,貌似信手拈来人人可为,实则,能率性写出绝妙文章的人,与能放胆喝得雄姿英发如坐春风的人,都非凡人,风徽足式。于前者,我心有所慕,虽明知前辈风谊难以企及,但既然视文章为盛美的事业,就只有放胆、放蹄直追,此外似无他法。我心恒定,如乡语所云:“瞎子看牛,死一拽着。”
自家意思
檐雨落在青石板上,作木鱼声。
旧年的丝瓜吊在木兰上。
金丝桃黄花照眼明,色艳而气清。
夏水浑浑茫茫,一路波折东进,站在河边望大水的婆娑老叟藏往知来。
檐雨、丝瓜瓤子、金丝桃、逝水和出尘又入世的老者,都有自家意思。天地化育万物,万物各有天命。所谓天命,自然禀赋也。仔细体察,日月星辰雷电霜雪,山岳湖海草木鸟兽,屋漏之痕,折钗之迹,冰凌之锋,晨露之凝,玉石之横纹,娇俏佳人之眼波,西楚霸王枪戟之厉风,莫不有自家意思自家面目。所谓自家面目自家意思,一家之言行,独有之风貌。
我友习书廿三载,以古今妙手为师,以北碑南帖为师,以造化自然为师,手摩心画日习夜练,砚中墨不干,手里笔常秃,主攻篆、隶之外,兼习楷、行、草诸体。观其字晋长多年,以为其篆、隶二体,风力雄朴气势端凝,渐近古人,渐近自然,也渐有自家意思自家面目。
习书之余,他课徒设教,诲人不倦桃李芬芳,山城书艺后继有人,有其功劳。
当年,张旭在邺城街市观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豪荡感激,得自家草书心法。索靖传张芝草法而变其形迹,骨势峻迈妙有余姿,创自家银钩虿尾字势。卫夫人《笔阵图》言:“自非通灵感物,不可与谈斯道也。”她说的是书法之道,其实一切文学艺术之道,“六艺”之道,旁及耕读渔樵之道,木、漆、瓦、铁、篾、焗、庖诸百工之道,莫不如此:非通灵感物,不可与谈斯道之神妙。所谓通灵感物,通而后灵,睹物兴感。
通灵,不是不易,而是太难。以书道言之,文字者,象形也,故而首当通文字之学,也即“小学”,知字形之所以然。其次当通古今书法源流变,知字势之所以然。又当通文章典籍、山川地理、自然物象、人情世事,尽窥众妙之门,养器识与气度。博而通,通而感,感而激,激而灵,然后才会成一家面目一家意思,才可以神游于尺幅之上,泻胸中之丘壑,泼纸上之云山。
大匠通灵。匠本是技,但匠之大者,其所操之技也是艺,也是道。大匠可以通天地鬼神。
我友心地敦朴,人也灵醒勤苦,其书艺精进指日可期。愿其通灵感物,符采克炳,早成大匠大艺大方之家。
(选自《安徽作家》,2022年第三期)
作者简介

储劲松,安徽岳西人,中国作协会员。作品见于《青年文学》《天涯》《山花》《长篇小说选刊》等,著有《雪夜闲书》《草木朴素》《黑夜笔记》《书鱼记:漫谈中国志怪小说·野史与其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