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2-11-29 来源:安徽作家网 作者:安徽作家网
近期,《收获》2022年第5期重磅推出我省作家赵宏兴短篇小说《来自古代的爱情》,引起评论界的好评,著名评论家北乔在《文艺报》2022年11月25日3版对小说作精彩评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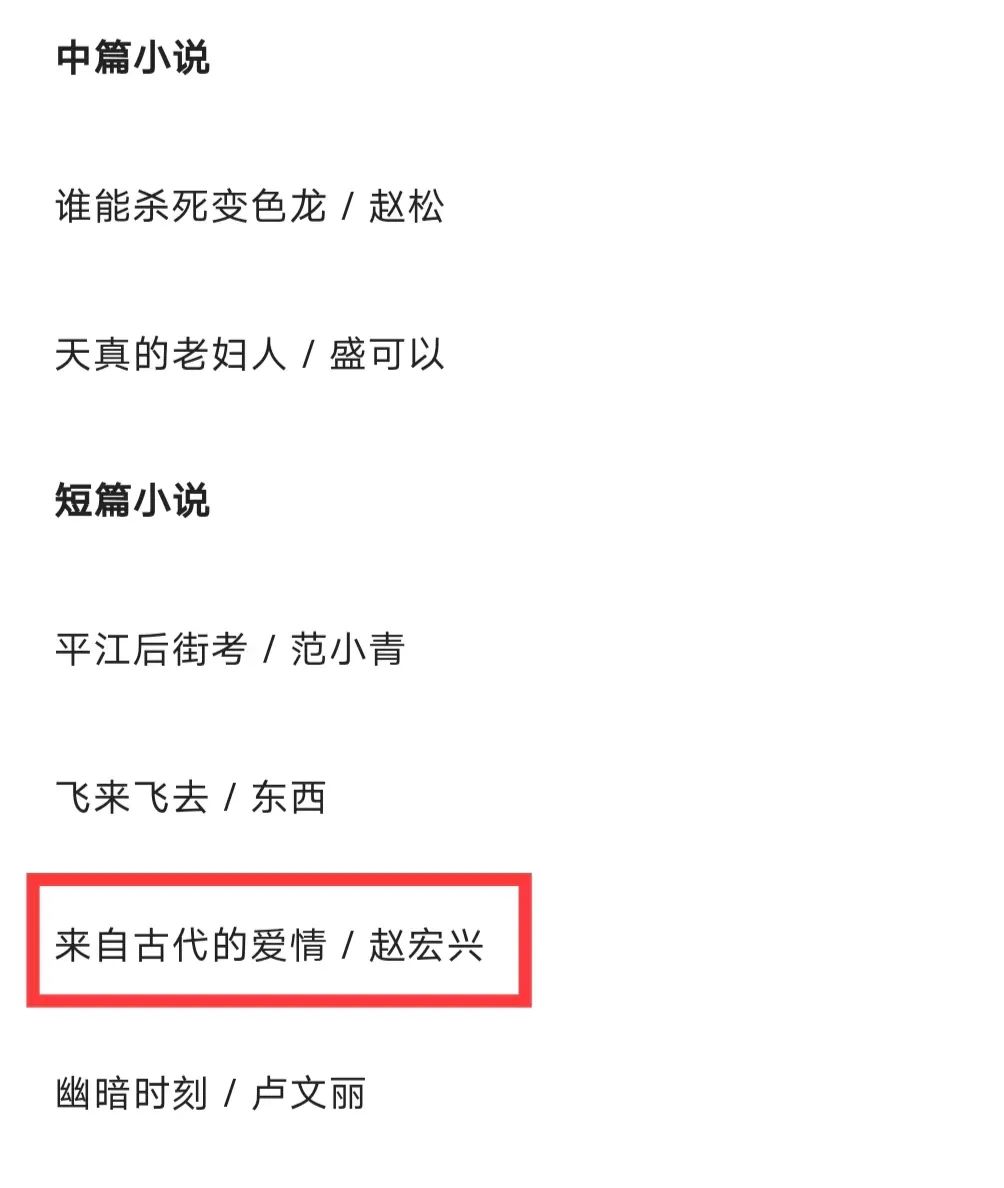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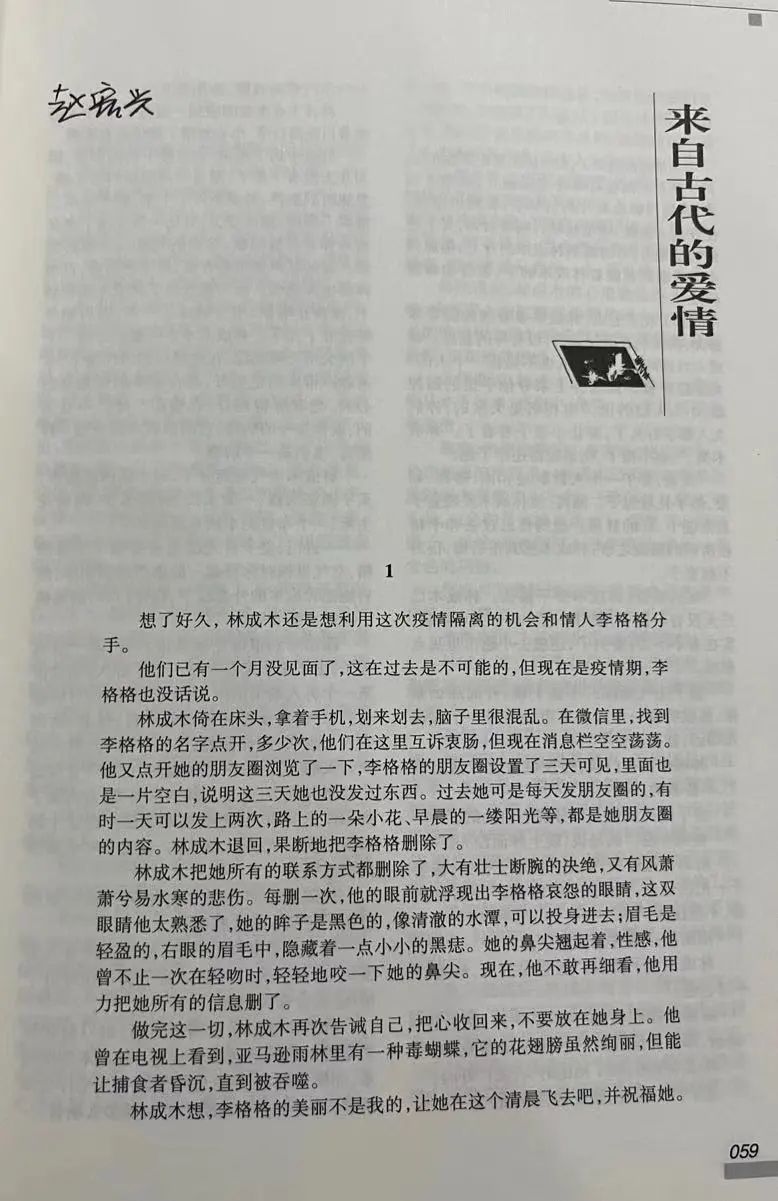
虚妄的自我确认与救赎
——评赵宏兴短篇小说《来自古代的爱情》
北乔
现实是小说的出发地,也是终极归宿。小说直面现实,快捷地让现时生活转化为文学叙事,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沉淀当下的生活,拂去浮尘,探索某些本质性的内在,继而让书写既与正在进行的生活互动,又能书写上具有文学性的价值,对作家对文学都是一个考验和呼唤。
赵宏兴短篇小说《来自古代的爱情》(刊《收获》2022年5期),虽题目中有“古代”,但是一篇与疫情有关的小说,并极具写实性的品相。非虚构性写作产生的亲密无间的现实感,让我们得以在文学的路径中进入实时的生活情境。主人公的经历,我们或许没有,但与他相似的困厄和苏醒,以及由此展开的纠结或挣扎,我们似乎都有过体验。小说本身具有完整的闭合性,但带来的阅读感受富有开阔性。
《来自古代的爱情》的情节并不复杂,林成木因处于居家隔离状态,失去了往常与外界密切互动的便利,继而才开始心力内收,关注家庭生活,发现了妻子的优点。内省的结果是心生愧疚,意欲与情人李格格断决关系。然而一有机会,他又与李格格恢复联系,并外出见面。在得知可能被同事行静传染了新冠嫌疑时,林成木感觉到事情要败露,准备跳楼自杀,以此了结一切。当行静确认其丈夫只是轻度肺炎时,小说结束,一个片段得以完整地铺陈,又有太多的意犹未尽。赵宏兴以从容的笔法,完成了生活与文学同质的跌宕起伏。
疫情给日常生活带来了诸多的影响,而“隔离”这一物理状态,既紧缩了我们的生存空间,又对心灵、情感和精神产生了压迫感。赵宏兴放弃了人性扭曲或异化、细节性神秘化的书写,而是将“困境”从表象中抽出,在另一向度叙述张力和隐喻之下的人性状态。小说中林成木的内省,并非是自我的觉醒,是在外力作用下的无奈之举。无法与李格格见面,甚至隔空联系,那个世界之于他是空白的,无效的。而居于家中,妻子的贤惠、儿子的可爱,让他有了温馨和踏实之感。曾经的虚空,此刻充实了。变的是他的心态,这暴露他人性中的自私。在虚实之间,林成木放弃了虚无,回到了现实。这根本不是觉醒,而是功利式的抉择。因而一旦这样的“困境”出现裂缝,他便会迟疑,甚至会恢复所谓的常态。
这篇小说的情节推动来自于“困境”的变化,基本上属于线性结构,这其实是意喻环境之于人的变化。但这样的变化,显然不是改变抑或叛逆,只不过是瞬间抹去了些许的尘埃,并未触及麻木的灵魂和浑浊的情感。我们看到了林成木与现实的博弈,但“困”与“突”的行为背后,有着令人惊讶但又极其平常的意味。当“困”成为主要力量时,处于下风的林成木开始收缩防守,并有所反省。反省的力度,与他本人无关,只取决于“困”的力度。当林成木为了减少对李格格的想念,带着妻儿外出游玩,他感受到家庭的暖意以及由坦荡所带来的幸福感。那一刻,他似乎要下定决心不再与李格格来往,站在山顶,面对原野,他高喊“我会成功的!”这不是向内的决绝,而是向外呼喊,显然这样的向“他者”的表白是苍白的,虚弱的。离开大地,立于山顶,尽管与家在一起,也喻示他不在人间,只在空无之中。一旦“困”势减弱,林成木会竭力寻求突围,回到以往的日常,从单纯的节奏坠入混乱的沼泽。
疫情妨碍了生活的日常,造成了诸多的“困”。然而在林成木的生活中,正常化的生活是“非正常化”的,“困”之中的内心和情感才是正常的,是符合道德和家庭伦理的,也是隐伏于他内心的“自我”。如果没有疫情之困,他在家庭与情人之间的生活摆渡依然会继续,且是他认为的正常的。疫情打乱了他自认为正常的生活态势,撬开了生活之祸。事实上,行静的丈夫也是因为疫情“困”住了婚外情。在非正常状态之下回到正常,而在正常状态之下有着太多或隐或显的非正常。这不是反讽,而是基于生活的清晰且不失真的镜像。因为敏锐捕捉到生活之中的非正常的正常,文学力量得以增值。外力挤压之下,看似无常,其实助力于清醒,这种与一般后疫情书写大相径庭的行为,令人耳目一新,更拓展了阅读的有效空间。
之于林成木的反常规行为,赵宏兴的书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反常规。也因为如此的对“困境”另一向度的审视,给小说带来了与众不同的价值,这是后疫情时代文学叙写值得观察的收获。他以极小的开口,切出生活的剖面,一切都是具实的生活细节,画幅小,但质感强烈。如此,他放弃了以古怪的想象力试图接气的方法,而是捡拾生活的本真,进行生活日常化的文学建构。那些意外所造成的反感,是坚实的叙事力,有力提升了阅读的驱动力,但种种意外又是生活中的日常所遇。这是故事走向、作家叙述和生活情节三者之间的逻辑交融,从而有了“小说写得不像小说”的生活气质和文学内蕴。
赵宏兴以与生活一样朴素的姿态进行的叙述,着重描写外在的撕裂,最终给林成木卸去重负,这是一个巨大的隐喻。再想一想小说的题目,明明写的是当下,却标为“古代”。赵宏兴的解释是,“百年之后,我们就是古代的人了,那时,是否有人会从中看到我们在一场疫情中的人生。”显然,作为小说家他,说出的话总是有所保留的。将“当下”标为“古代”,他真正的意图当是林成木这样的人,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时间在这里已经失去了意义,无论何时,这般困之挣扎的图景都在。遭遇困境,我们有很多的处理之道,然而终究无法借助外力来实现救赎。就像本要自杀的林成木会重新回到生活中,无论疫情在或不在,他如此的虚妄之路还将继续。“林”成“木”,看似是因为疫情所带来的阻隔,他孤独了。还可以有另一种指向,这就是当一个人从群体中抽身而出,他需要面对生命中的所有。而当汇入人流中时,便认为受到了某种庇护,进而将自己的身影隐藏,更消解了内省和救赎的良知。
如此,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篇与有疫情有关的小说,但又是一篇与疫情无关,精确指涉了现实中某种病相,挑战了潜于生活之里的某种见怪不怪的恒常。
小说的开始,林成木是紧张的,而我们怀有期待,期待在特殊境遇中,林成木能够清洁灵魂,找回自我,踏上救赎之路。小说的结尾,林成木获得了解脱,而我们的沉重才真正开始。当得知过往是虚惊一场,林成木暂时脱离了因疫情而来的风险。“林成木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澎湃的生活气息重新扑面而来。”林成木又重新抛弃了自我,融入丛林之中,所谓的救赎就止中断。这“澎湃的生活气息”里原来尽是无所顾忌的欲望和无从修复的秩序。
作者简介

北乔,江苏东台人,评论家、作家、诗人。出版文学评论专著《约会小说》《诗山》、长篇小说《新兵》《当兵》、小说集《走火》《天要下雨》、散文集《远道而来》《三生有幸》、诗集《大故乡》《临潭的潭》等二十多部。曾获第十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黄河文学奖、三毛散文奖、林语堂散文奖、海燕诗歌奖、刘章诗歌奖等。现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