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4-28 来源:安徽作家网 作者:安徽作家网
近期,我省作家万以学散文集《城市的笑容》由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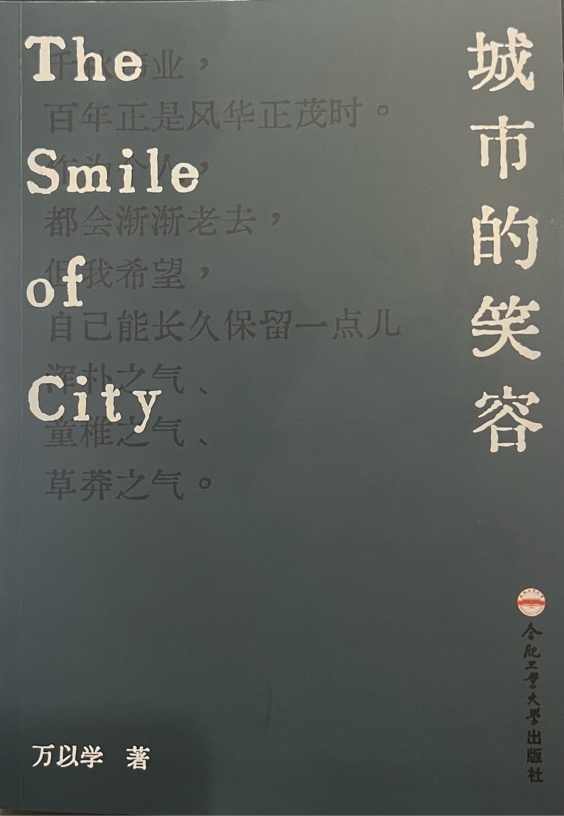
爬山记(节选)
一
2022年元旦,在合肥与陈剑先生夫妇餐聚。他俩都是从铜陵走出去的佼佼者,且一直对铜陵抱有极深的感情。席间,聊起我们的父辈。陈剑父母是干部,我父母是地道工人。在那个开发矿业的时代,他们都是铜矿的开拓者,铜陵市的开埠者。我们一致认定,我们父一辈的共同特点是生活特别艰辛,但对工作都投入了百分之百、甚至百分之二百的热情与干劲。那是一种真正全身心的投入,以至他们对我们这下一辈,都没花过什么特别的精力管教。
这唤起了我的记忆。告别他们我回到铜陵,便约了老友稻田和橡树,去爬笔架山。我习惯叫爬山,不叫登山。象笔架山这样的山头并不十分高峻,也没什么名气,说登字总觉太庄重,再说我小时候这山上没有道路,手脚并用的时候常有,此外,爬既有上的意思,也有下的意思,还有在山上横着走的意思。用爬字虽然俗,但贴切。说文乎一点,它比较适合矿山子弟尚未觉醒的身份意识。
我们从立有“工人公园”字样牌楼的地方,开始爬山。冬天的山,有些萧瑟。山上很少游人,只有三二个锻炼的人。上山的台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修的,一色青石条,垒得平平整整,有的上面已或多或少积累些青苔,看上去已经有苍桑感了。路径也没有营造迂回曲折,而是依照山势,笔直地伸向山顶。漫山植被很茂密。林叶落尽,除了松树和部分竹丝保持着绿色,竹丝是一种不能成材的小竹,丛生,生命力挺顽强。但那是似披着一层白霜的苍绿,不是春天的那种青翠。沿笔架山脚一周,绵密地植着黑松。这种黑松,长起来很慢,俗称不老松。这些松树还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种植的,转眼过去六七十年了,仍不见高大。在黑松林的边缘,杂树已生长起来,间或还有十分高大的树种,颇有原始次生林的模样了。林下则是缠绕在一起的荆刺藤蔓和竹丝。它们横七竖八,封死了上山的各种小径,使我们只能沿铺设的青石路行走。
记得小时候,这松树林下和未种植松树的笔架山上半部分,都是清朗朗的,是稀稀的杂草和灌木。那时居住在笔架山下的工人子弟,有一个不是规矩的规矩,就是放学后上山砍柴。当时这笔架山是封山的,正式称呼为“封山育林”,我们认为育林主要是山脚下的人工种植的松树林,至于山上的那些杂树灌木野草,是延伸受到保护,顺便被封的。矿上下了很大的决心,专门成立了由伤病残工人组织的护林队,还沿山脚,以种植的松树林为界,拉了一道铁丝网,阻止人们上山砍柴。砍柴这个词不是很准确,也可以叫割草,但因为不仅是割野草,也砍混在野草中的杂树和灌木,而且砍字比割字更显得用力气,所以我们通通叫砍柴。只要上了山,我们是什么都砍,甚至连松树的枝桠也敢削,但不敢砍松树主干。砍松树主干,就是砍掉了一棵树,真是破坏植树造林了,那是犯罪行为。所以搞到最后,笔架山的松树林,只有上面树冠一小片是绿的,下面都是光溜溜的树干,显得林间空荡荡的。我们这帮子砍柴的家伙,与矿上的护林队形成了长期的拉锯战,总体上我们赢得多。据说,矿上的护林队因为保护不力,没少挨矿上的批评训斥。护林队员都是工人,在某程程度上,他们对我们的行为是睁一眼闭一眼的。但这事儿,我长大后才明白。
当时我们还发明了两个专有名词:叼树棍子和挖树桩子。所谓叼树棍子,即拿把镰刀,专门去找灌木杂树,然后把它们挑(叼)出来砍掉,凑齐一小捆后背回家。这些灌木虽不是木材,但烧起来火力大、火力猛,几根就比得上一捆野草。人们都说,树棍子烧出来的饭也香。但我从未注意到。挖树桩子,就是挖树根,当然不是挖树根做根雕盆景,而是山上柴草都被砍完了,只得把埋在土里的野树灌木的根挖出来,它们比野草、甚至比树棍子都耐烧好烧。现在回想,这对生态的破坏是真正彻底的。
我家住的地方在笔架山西北麓的露采新村。七十年代初中期,矿上的生产任务愈来愈重,村里的人口也愈来愈多。矿上在原来的居民村边上,象摊大饼一样,顺次又盖了些新平房。新居民有从工人新村、杨家山村迁来的,还有复转军人、新来的技工,还有“农转非”,即矿上从农村新招来的农民工。每家都得找柴火烧饭,所以我们砍柴的地点也越来越远,笔架山加上周边的罗家村一带,甚至田埂上的野草都被搜罗一空,有时大人们还得跑到812队和大倪村、小倪村那边,才能砍到一点柴火。
直到七十年代中期后,情况起了变化。国家因为煤炭生产量上去了,开始为中小城市及普通城市居民家庭供应煤炭。煤球开始进入普通百姓人家。许多人家这时开始放弃烧柴火。只有真正贫困家庭,还在为了节约一点煤钱,坚持去砍柴。到我七八年上大学时,基本上就没有人再去砍柴了。很多人家依旧保留了柴垛,但很快它们就变成了垃圾。没有人再用柴火烧饭了。真正的改变是八十年代中期,铜陵开始推广烧煤气。山上的柴草没有人去砍,植被便得到快速恢复。铜官山矿发展也进入新阶段,资源枯竭,闭坑关破,护林队变得有名无实,没有人管山林了。还引发了几场山火,烧死了人。听说,后来干脆放开了,铜陵县洲圩地区和江北地区的人们可以自由上山砍柴,再后来,因为防火需要,想花钱雇人上山砍柴,也雇不到人了。
柴米油盐酱醋茶,柴摆在第一位。在传统社会,自然界提供的柴草类燃料,无法供养日益增多的人类,更是无法保护生态环境。我读过西方传教士写的一本书,描写的是二十世纪初华北的初冬,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看不到任何垃圾,每一片树叶、每一根草、每一砣人畜粪便都被人拣拾回家,少数用作肥料,大多用来烧饭了。反映的就是农耕时代,人们燃料紧缺的生活。从理论推断,只有煤炭、石油等化石燃料才能满足时代需求。这也是农业国家必须转变成为工业国家的内在要求。
笔架山的草木春秋,就是这段历史的一个侧面证明。
二
前些年因工作关系,我的膝盖因爬山受过伤,自此心里便留下阴影,对爬山有畏惧感。但这一次,不知不觉中,我们就爬到了山腰,继而又爬到了山顶。我直怀疑这笔架山是不是变矮了。我仔细观察,发现这笔架山除了我们走的这条路线,它的山脊线确实塌陷了。那是因为开发矿山、人们在山肚子里的挖矿,而造成的地表崩塌。如笔架山主峰北侧的山峰,原来只比主峰稍矮一点,现在看去已矮去了一大截。它崩塌的痕迹还在,只是被茂密的植物遮蔽了,不仔细分辨,不大容易看出来。
笔架山的山顶标志,是个碉堡。这碉堡不知什么时候修的,反正我记事时它就在这里。碉堡的基础部分用大片石砌就,水泥沟缝,上半部是青砖和红砖,再加一个水泥平顶。砖墙部分,朝四面开了四个瞭望孔或射击孔,因为很大,甚至可以称为瞭望窗了。原来在大片石和砖墙部分,镶嵌着钢筯做成的爬梯,可以上堡顶的平台。现在这钢筋爬梯已被拆除了。片石和青砖红砖上,满是来此一游的人涂的鸦。但碉堡内外很干净,看来不仅有人打扫,爬上山的人也很注意卫生。
这是个瞭望的好地方。铜官山因有笔架山的间隔,也不具备这里的观览条件。站在这个制高点上,整个铜陵市尽收眼底,一览无余。西南方向的铜官山、宝山,尽管在它们身上还能看到露天开采的痕迹,但并不损害它们的高大巍峨。北边有一道亮闪闪的细线,那是长江。东边和南边,是整个铜陵市区,一片片的高楼接到天边去了。虽有低矮的螺丝山等,但不影响视线。
我们俯视笔架山下,城市的发展脉络似乎都隐约可见。
围绕着笔架山,从东面始,依次是解放东村、解放西村、和平新村、友好新村、工人新村、长江新村、露采新村、平顶山村等......然后越过铜官山、金口岭矿的废石堆场和著名的铜官山矿露天采坑大洼凼,和解放东村相接,形成一个居民村环带。废石堆场经过整理,现也被开发出来,形成了大片的住宅楼。在铜官山和笔架山之间的废石堆场边,曾经建有赫赫有名的铜陵啤酒厂,如今也变成了居民住宅楼。历朝历代诗人骚客们所谓的沧海桑田、山河变易,在我们这个时代,却是短暂人生肉眼可见的速度。
从开发矿山滥觞,这些陆续兴建的系列居民新村,系统而鲜活地展现了铜陵独特的历史发展风貌。它是城市的初始生长点,城市从此开始其自我生长的生命旅程。后来它又成为城市的主体部分,清晰标示了它后续的发展轨迹。如果把这些新村放在新中国的时代大背景下看,它是一种与政治、与社会、与产业发展紧密的关联事件。它既具鲜明时代特点,从解放、和平、友好等等名称上,基本上也能猜出它们建设的年代。把城市、特别是新建城市为产业工人兴建的新居民点命名为村,而不是什么街、巷、弄、里。据说新中国的第一个工人新村产生在上海,是依托一家新建工厂设立的。也有传统的影踪,村本来是用来命名农民生活聚落的,现在却用在了城市,只是这些村前冠了一个字“新”,以示与农村的村落“村”区别。不知是不是与这里的居民大部分人来自于农村有关,还是与要消灭“三大差别”的无产阶级文化概念,如“公社“等等有关。当然,最重要的是一大批山南海北的人,北到辽宁、山东,南到浙江、福建,东到上海、江苏,西到湖北、河南,安徽省内各地市,包括高级领导干部、专业知识分子、退伍复员军人、工人、农民等等,曾合成聚集居住在这里,他们共同生活、工作,创造了城市,创造了属于自己独特的文化,包括政治组织、家庭制度、经济制度,以及生活方式、休闲娱乐方式等。在全国各类城市发展中,只有新中国建立之后成立的少数几个工矿城市才是这样,显得非常特别。
人们在这里欢笑/在这里哭泣/在这里活着/也在这里死去/在这里祈祷/在这里迷惘/在这里寻找/在这里失去(汪峰《北京北京》)。
铜陵没有所谓的大型古代城市遗址、特别风格建筑,没有挂上牌子的文物保护单位种种,但这些简单粗陋的工人居住村落,真实、完整地隐藏着这座城市的生命本源和遗传密码,积淀、容纳、镕铸了自己城市独特而丰厚的历史文化。城市独特的灵魂,与它历史环境风貌的相关联系无可置疑。
我们今天看不到村了。触目所及都是香格里拉、维多利亚、皇家、花园、公馆、别墅、洋房之类,取名要么很洋气,要么很古典,当然最后都归为某某社区。
……

万以学,安徽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学士,中央党校经济管理专业本科,安徽大学国际贸易专业研究生,美国马里兰大学高级行政管理研宄生,香港理工大学品质管理专业硕士。长期从事觉政工作,曾任铜陵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主任兼市外商投资局长,铜陵市副市长、常务副市长,黄山市常务副市长,淮南市委副书记,省旅游局局长,省旅游发展委员会主任,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兼省政府侨务办公室主任。现任省政协常委、民族与宗教委员会主任。发表有关区域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等研究文章若干篇。1992年,牵头组织撰写《醒来铜陵》,获中国新闻一等奖。著有《谁与年锋》《如此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