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6-21 来源:安徽作家网 作者:安徽作家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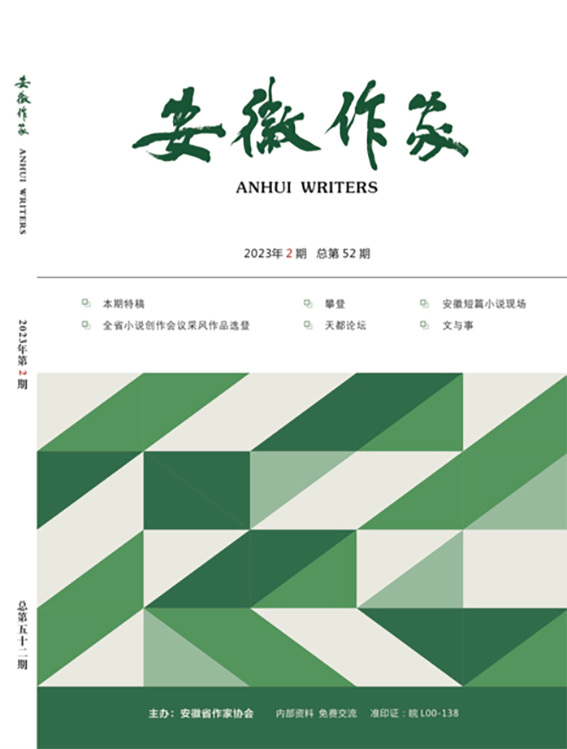
作品欣赏
木字旁们
夏 群
洪枫第三次打来电话,说那些木头家伙差不多修补完了,接下来就是修缮老屋了,问杜椿什么时候有空,回来商量一下,他不知道老屋哪里该动,哪里不该动。
杜椿正坐在办公室里赶一份领导要的材料,洪枫说话的时候,他的右手操控着鼠标,将文档的进度条上上下下地拉,像锯一根湿木头,赶材料时那股一直被压迫着的心烦气躁也借机蹿出来,他一边在文档最后重重地敲了七八个毫无意义的回车键,一边说:“我最近很忙,明天还要出差,你自己看着办吧。”想想又补充道,“需要钱再和我说,就这样。”
掐掉电话前,杜椿听到洪枫那句像从遥远的时空甬道中传来的声音:“椿儿,不是钱的事,我怕师父不满意……”
杜椿他们这个家族,从太爷爷杜松那“一棵树”开始,就慢慢繁衍生息,长成了一片森林。这片森林里,树种各异,除了松树,还有榆树、楝书、桐树、樟树、梅树、桃树等,喜好和脾性不一样,但扎根在同一方土地上,共享着同一片蓝天,吸纳同样的阳光雨露,骨子里的他们,其实都是一个品种。
杜椿小时候很嫌弃这个像女孩子的名字,因为小伙伴们叫他“椿儿”的时候,故意强调儿化音,还把尾音拖得长长的,然后猖狂地窃笑。父亲说他是捡到宝了却当草,香椿木虽不是红木,却是一等木材,质地坚韧,是百木之王,他应该庆幸这个名字没有被姐姐和其他堂兄弟姐妹用掉。
他们家有一张香椿木四方大桌,配了同是香椿木的四条长凳。桌子和凳子做工都很精细,桐油上得也足,泛着幽光,大桌四角那里还做了镂空的花节雕刻。桌子和凳子放在堂屋的中央,正对着江山红日中堂画,很气派,家里来人总会夸上几句。杜椿对家族里以木起名这个传统一直不以为然,他说,如果按照树的品种去给后代取名字,再去掉那些所谓的凶树和寓意不好的树,诸如柏、柳之类,只会越来越难取,而且越来越次。父亲说,那么多树呢,得管多少代啊,再说了,木字旁也行啊,都与木有关。四方大桌和长条凳的香椿木材,来源于他们家的老屋院子边依着坎沟歪斜生长的香椿树,现如今还存有两棵,长得很是高大繁茂。
父亲很爱吃香椿芽炒鸡蛋,初春时节,他会在长长的竹竿上端劈开两个口子,形成一个三角叉,轻而易举地别断高高在上的香椿芽。杜椿小时候拒绝吃这道菜,除了他受不了那股奇怪的味道外,也因为他下意识觉得那是在吃自己。夏天的夜晚,杜椿喜欢翘着二郎腿躺在竹床上在树下乘凉,透过香椿树密密匝匝的羽状复叶看星空与银河。上大学离开故乡后,他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去看夜空了,仿佛自那以后,星空与银河在他的生命里就消失了,连带着那两棵香椿树也消失了。
当年妻子怀孕,父亲说,如果是男孩,就叫杜檀,如果是女孩,就叫杜榕。杜椿和妻子都不太喜欢这两个名字,儿子出生后,他只将“檀檀”用作儿子的小名,而户口本上的大名是妻子花了200块找一个周易风水大师按生辰八字给取的,和树木不沾边,和木字旁也不沾边。父亲知道后,有些生气,说他怎么能自作主张轻易打破这个延续了几代的传统,责令他去给孩子改名。但名字还没来得及改,杜椿堂弟的孩子也出生了,取的名字也没有遵守这个传统,叔叔杜楝倒是开明,并未多说什么。杜椿便有了借口,给孩子改名的事也就一拖再拖。
杜椿的太爷爷、爷爷、父亲、叔叔,都是木匠。
村民们用“三杜”来形容杜家这同是木匠的祖孙三代。从建造房屋时用的木头屋架、门窗,到三门橱、五斗橱、书几、雕花床、立柜、木桶、木盆等传统木家具,再到犁、风车、水车等农具,村里每户人家甚至周边村里人家都一定能找出几样出自“三杜”手下的木器。经过时间检验,口碑、手艺最好的是“杜二”,也就是杜椿的爷爷。村子里一个上了年纪的婆婆还经常把“我家里那个高低橱是杜二打的,几十年了,还好好的”挂在嘴边。“杜二”最擅长的是农村的老式房子里的露明梁架,卯榫坚牢,梁、柱等交接处的斗、拱、驼峰等装饰很美观。人们不叫杜椿的太爷爷杜松“杜大”,而是叫他“杜师”,这个称呼里包含着他们对杜松的最高褒奖,毕竟手艺最好的“杜二”,也是“杜师”带出来的。“杜师”遗留在人世的作品不多了,仅存几件,也是经过“杜二”或“杜三”修补或翻新过的。
杜椿的父亲杜榆能够“打败”弟弟杜楝成为“杜三”,不是因为手艺更胜一筹,而是因为脾性,杜榆性格虽沉闷,但行事也稳重,杜楝的性格有些张扬,好酒,所以在人家做活时容易耽误事,一次给别人家屋上梁时,出了些纰漏,让主家感觉触了霉头,从此失了信誉。对于没能得到“杜三”的名号,杜楝表现得好像也不甚在意,有绘画天赋的他后来去了苏州一家红木雕刻厂,从事红木雕刻工作。他在雕刻厂工作,收入远高于在乡村做木匠时,他们家也是村里第一个盖三层楼房的。杜楝后来劝说过杜榆和他一起去苏州,大意是说传统木工艺没什么市场了,工厂都量化了,还守在村里干什么,“杜三”的名头真有那么重要?杜榆干脆地回绝了他后,杜楝就再也不提这茬了。
每个人心中应该都有一幅关于父亲的形象画,杜椿心中的那幅画,时间背景总是在清晨或者黄昏,父亲行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右肩上背着一个简陋的工具箱,右手上还拿着一个锃亮的锛子,左臂上套着两把大小不一的锯子。父亲从来都是早出晚归,家对他来说,就像一个长租的旅馆。不出工的日子,父亲也不怎么照看田地,除了犁田打耙,家里的农活都是母亲一个人担下的,他总是一头扎在那间堆满各种木料、工具、半成品木器,充斥着各种木材味道的披厦里。
杜椿觉得,父亲对那些工具、木料和木器的关心和爱,胜过对他和姐姐杜桂的。
出差回来的高铁上,因为车马劳顿,缺少睡眠,杜椿的头有些疼,正闭目培养睡意,洪枫发来微信,有语音、文字、图片,还有一段10秒钟的视频,它们像密集的子弹一样射进杜椿的脑袋,使他头疼加剧,有炸裂般的感觉。即使不听语音消息,不打开视频,杜椿也可以根据“椿儿,你说呢?”那几个字判断,这些无非都是洪枫在传递同一条信息,有时间回来看看,他一个人真做不了主。杜椿知道,这不过是洪枫的托词,以他的行事风格,绝对将一切都规划好了,只不过他需要自己参与决策,从而分担一半责任。
小时候,父亲也曾经热切地培养过杜椿对木匠手艺的兴趣,因为他希望栽培出一个“杜四”。他不光教杜椿识别树的品种,还让他通过已经解板的木材去辨别是什么树,后来,升级到让他通过木屑去辨别。他告诉杜椿,椿树的木屑是浅棕色的,能闻到香椿芽的清香;松树的木屑颜色淡一点,但有着松节油的香味;柏树的木屑接近白色,有一股柏枝的幽香,水杉和白杨树常常是湿的时候解板,木屑潮湿,捏在手心能成小团,但松手即散……
比起识别树木、木材或木屑,杜椿对父亲那个墨斗更感兴趣。墨斗是一条鲤鱼形状,脊背上靠近头部的地方开了墨池,靠近尾部安装了墨轮,墨线从微张的鱼嘴中吐出,前段挂着一个“8”字形的铜班母,两个腹鳍与一个臀鳍形成三角底座,能让鱼能稳固地站立。臀鳍和尾鳍中间,隐藏着收线小手柄。虽然黑乎乎的,有些磨损,但依稀可辨鲤鱼眼睛有神,鳞片逼真,尾鳍线条流畅,仿佛游动于水中。这个墨斗是太爷爷亲手做的,之后传给了爷爷,爷爷又传给了父亲。父亲告诉杜椿,墨斗虽小,但制作起来却不简单,各个部分需要单独制作,主体还需要一木连做,费工费时,对于木匠来说,墨斗代表的是祖师爷鲁班,是有神性的,这个鲤鱼墨斗要当成传家宝传下去。
鲤鱼墨斗里有少年杜椿寻思不解的东西,于是他总喜欢趁着父亲不在意偷拿墨斗,摇摇线轮,抠抠墨池里的棉花,四处乱弹寻找奥秘。一次在父亲要用的板材上弹了很多黑线,又把松动的小手柄弄丢了后,父亲非常生气,不怎么动手打孩子的他,用木卡口抽了杜椿的屁股。杜椿反驳说,不是说墨斗要当传家宝传下去吗,早一点传给我不行吗?父亲说,那要等你学会木匠手艺再说。杜椿再也没有摸过墨斗,包括父亲的其他工具,以此来告诉父亲,他不会学木匠。
晚上躺在床上,杜椿才点开了洪枫发的那个视频。视频中环拍的是父亲的工作间,工作间的前身是杜椿的房间,当初靠着床的那面墙上,钉有四排木条,木条后面有空隙,插别着工具,木条上面钉有长铁钉,根据形态大小整错落有致地挂着工具,这些工具有一大部分是父亲根据自己的使用喜好做的。杜椿看到了锯子、刨子、凿子、蜈蚣耪的身影,当镜头最后一晃的时候,他捕捉到了杂乱的工作台边缘,那个黑乎乎的鲤鱼墨斗的墨线从口中扯出一截,“8”字形的铜班母悬吊在空中,微微晃荡着,像鲤鱼痛苦地吐出了自己的内脏。
他给洪枫回信息,工作间先别动,他周末回来。
杜椿的老家在潜川县城以东一个国家4A级森林公园的山脚下。前些年美好乡村建设,对村子里的环境进行了整治和规划,村子现在是面貌一新,但即便如此,也没有拴住年轻人飞翔的翅膀,包括杜椿。杜椿没有什么故乡情结,可能与脱离故乡后的生活一直过得顺风顺水有关。
杜椿工作之前,他们一家人都住在那所由石头、青砖、小黑瓦和出自“三杜”手下的木器构成、填充的老房子里。千禧年的时候,家里在进入景区的路边新盖了楼房,母亲就在家里摆了个玻璃柜台,门口摆放了一张木桌,开了一爿小店,卖矿泉水和香火(景区山顶有一座寺庙,是江淮十大名寺之一)。老房子空下来后,父亲把他的工作间从披厦搬到了杜椿之前住的南头的房间里。
村里人家的房子越盖越漂亮,有几户人家甚至花几十万盖了豪华的别墅,安装了铁艺的庭院大门,买了成套的、有着精致花纹和软包的家具。每当看到哪户人家的院子一角或是放杂物的耳房里堆放着弃用的老木器家具,父亲都想着把它们“赎”回去,久而久之,村里人会主动把淘汰掉的老家具送到父亲那儿,老房子渐渐被缺胳膊少腿的木器家伙占领,成了木器回收站。
八年前,杜椿听人说村庄要征收拆迁,他出钱让父亲把老房子边的披厦、猪圈、鸡舍拆了,盖了四间两层的小楼。又找来挖掘机把老房子边的一片水竹林翻了过来,连带着之前的稻床,都栽上了桂花树,有近千棵,想着到时候征收的时候,桂花树按棵赔偿,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可是好多年过去了,村庄安然无恙,只是规划了道路,升级了一些硬件设施,将一些人家的外墙刷了,画了壁画。那些栽种得过密的桂花树因为地盘拥挤,身材纤细,不成气候,连买主都找不到。两层小楼后来租给几个外地的承包责任田的种植大户住家了。
杜椿到家后,发现之前堆放在老屋里的那些残疾木器基本都修理好了,整齐有序地摆放在那两棵依然茂盛的香椿树下和小楼一层的屋子里,木犁、木耙、木锹、风车、木桶、木桌、三门橱、五斗橱、梳妆台、洗脸架、木质窗格子、雕花床,踏板打稻机等,甚至还有一个以前杀年猪时烫猪用的杀猪桶。除了杀猪桶,每样木器都不止一个,木犁至少有二十把,列队的士兵一样等待着检阅。这些东西之前堆在老屋里不起眼,现在修理好排兵布阵一般摊开,居然有如此大的阵容,杜椿难免有些吃惊。
洪枫正在修一个龙骨水车,水车的送水叶片新补了好些块,虽然他选择的木材接近水车本身的老旧颜色,杜椿还是一眼就看出来了。
胡子拉碴的洪枫看了一眼杜椿说:“椿儿,回来啦!你等一下啊,马上好。”
“你速度挺快的,这没几天,都修好了?”杜椿问。
洪枫没抬头,继续手里的活计,解释道:“不是,很多东西师父应该一收回来就修好了。”
记忆中的一个场景突然跳出来,地点也是在这老屋的门前。
那应该是小学五年级时中秋节的早晨,杜椿坐在小板凳上吃早饭,父亲正收拾他的工具箱。这时候,一个中年人领着一个初中生模样的男孩子来到他家,中年人手上提着的红色塑料袋里,应该是烟酒。男孩子左手上提着一刀用稻草系着的肉,正打着旋,右手上提着一条草鱼,稻草从鱼鳃穿过鱼嘴打了个结,系肉穿鱼的稻草绳上,都穿了一块四方小红纸。
中年男人大着嗓子喊了声:“杜三师父。”然后将男孩子手中的鱼和肉拿过来,连着手中的袋子,一起递到父亲手里,“拜师礼你收下,孩子就拜托你了,不听话你就打。”然后用眼神示意那个男孩到前面来,说:“叫师父。”
男孩走过来,脆生生地叫了声:“师父。”
这个男孩叫洪先进,父亲的第一个徒弟。
父亲一边和洪先进父亲寒暄,一边继续收拾工具箱,还不忘将手中的鲤鱼墨斗扬了扬, 说:“这墨斗还是我爷爷传下来的,有灵性了。”说完很小心地将墨斗放在工具箱最上面。
父亲问洪先进:“你喜欢什么树?”
洪先进想了一会说:“红枫。”
父亲又问:“你还知道红枫,为什么喜欢?”
他说:“班级的窗外栽着一棵红枫,每天看得多了,就喜欢上了。”
后来,有个晚上躺在床上,洪枫告诉杜椿,他是爱屋及乌,因为他喜欢的一个女同学特别喜欢红枫,没事就对着班级窗口那棵红枫发呆,还摘红枫叶当书签。
父亲说:“那正好,你又姓洪,以后在我这儿,我就叫你洪枫了。”
那天父亲还对洪枫说:“对木工来说,工具就是我们的武器,而且木工的聪明才智,不光在我们打制的木头作品中,更在我们的一锯一锉中,一刨一耪里。”
这句话后来杜椿听过很多次,背得滚瓜烂熟,很久以后杜椿才知道,父亲的这句话多么有深意,完全不像出自榆木疙瘩一样的他口中,但想着父亲是一个如此痴迷木头的木匠,又觉得他理所当然能有这样的境界。
洪枫直点头,眼睛亮晶晶的,用一种近乎崇拜的眼神看着父亲。
洪枫成为父亲的徒弟,和父亲一起早出晚归,甚至住到了杜椿家,父亲给他打了一张松木的单人床,就放在杜椿的房间里,和他的床形成直角摆放,这一住就是5年,直到他出师。洪枫话多,人很勤快,头脑也灵活,深得父亲的喜爱,他学手艺的同时,还帮忙家里干农活,又讨好了母亲,他在家里如鱼得水,俨然杜家一分子。
青春期的杜椿叛逆得很,没有个读书的样子,门门课都难及格,特别英语,常考个位数。初二升初三的那个暑假,父亲说,本来以为是椿树,没想到是棵泡桐,你不是念书的料子,别念了,跟我学木匠吧。洪枫说,好啊,这样我也有师弟了。被父亲说,杜椿本是无所谓的,反正听习惯了,但他被洪枫的这句话激着了,他明确表态,绝对不会学木匠,之后,他用发愤图强为自己的未来开辟了一条逃跑的路径。
虽然年纪相差不大,住在同一个房间好几年,但杜椿和洪枫一直没有成为很好的朋友。没有洪枫的时候,父亲不怎么管姐姐和他,平时也很难得说上话;洪枫来了,父亲也依然不管姐姐和他,但他不再惜字如金,话变得多了起来,只不过说话对象是洪枫。堆满工具、木料和半成品木器的披厦里,总是传来他们使用工具的声音,说话声,偶尔还有笑声。
杜椿这时候发现,父亲对洪枫的关心和爱,也胜过对他和姐姐杜桂。杜椿对那些夺走了父亲的关爱的木头们无计可施,但对洪枫,他可以宣泄自己的不满。一次当父亲对着那些工具,重重叹口气后说,传了三代的手艺,到他那辈要断了的时候(姑姑和叔叔家的孩子们,也没有人接这个衣钵),杜椿呛他,不是还有洪枫吗,你不是说他虽然不姓杜,但就是“杜四”吗?父亲竟然没有反驳,这更让杜椿生气,无形中将洪枫放在了敌对位置。
洪枫出师后,估计因为不好意思,没有再住在杜椿家,但并没有单干,还是和父亲一起做活。一开始还好,后来母亲也有了些怨言,当学徒的时候不拿工钱,但出师了还绑在一起,需要付他工钱,等于从父亲的饭碗里抢饭吃。父亲却不准母亲在洪枫面前说什么,还说她小肚鸡肠。
乡村木匠手艺衰落的时候,洪枫创办了一家半自动化木器加工厂,生意越做越大,潜川县城的好几个家具城的家具都是他在供应。母亲向父亲念叨,洪枫他现在生意做得那么大,怎么不念着你这个师父,给你在厂里搞个职位还不是他一句话的事。父亲说,他做得再大,靠的是他自己的本事,和我这个师父有什么关系。
三十年过去了,还是在当年的位置,此时洪枫的双脚埋在地上一堆卷曲的刨花中,黑衣服上群星般散落着锯末,头发上还粘有一缕疑似蜘蛛网的东西。好久没见了,杜椿有点不敢相信,这个人居然是那个拥有一家半自动化木器加工厂的老板,毕竟之前去他的工厂参观过,他颇有些大老板的派头,其次,杜椿以为修补这些木器,洪枫是要指派给别人干的,毕竟他的工厂里最不缺的,就是木匠。
“这大概是你们村里最后一个水车了,有了水泵后,这东西就淘汰了,很多人家都卖掉了,块头太大了,占地方。”见杜椿不出声,洪枫又问:“椿儿,你车过水吗?”
杜椿想起来高考后的那个暑假,他和父亲一起车水的情景,他和父亲一人在左一人在右,循环往复地用手拉动连杆,将水从池塘抽到一个叫五斗的田里,田里的晚稻秧苗插下去没几天,才定根。他的胳膊酸痛得厉害,身上被蚊子咬了很多包。明知道他不感兴趣,父亲却还在喋喋不休地说龙骨水车的制作原理和特点:由车箱、送水叶片、车毂、手摇把组成,有两层,下层的叫木水池,上层的叫花格,水车用杉木最好,但取水叶片,用柳树木最好。
眼前的这个龙骨水车,就是当年的那个吗?杜椿弯腰,用手摸了摸水车,心里有一丝触动:“车过。”
除了父亲的工作间,老屋已经空了,还没来得及打扫,有让人心里一沉的狼藉。站在父亲和母亲曾经的卧房里,杜椿在心中还原着当年的场景,他站立的那个地方,以前是放床的位置,他和姐姐都出生在这间屋子的那张床上。
洪枫指了指房顶说:“这上面的椽子需要再加固,再刷些防腐防虫漆,上面的瓦我看了一下,很多破损了,所以屋里好几处漏水,我看干脆换成红瓦吧,和小楼的也统一。”
洪枫后来说了很多自己的建议,比如把原本的院墙修整一下,院门做一个徽派木雕的仿古飞檐门楼;院子里铺上木板;靠近椿树边,安一个六角凉亭;老房子原本的对开老式窗户不用换,但玻璃要换;地面是土质的,虽然很有历史感,但是潮气影响木器的存放,需要重新整理铺上地砖;外墙不动了,但内墙需要修整粉刷;老房子里就摆放日用木器,小楼里摆放农具,小楼的屋子还需要打通各个房间的内墙,这样方便游客参观……
“这样行不行,你也说一下你的想法。”最后,洪枫问杜椿。
过了这么多年,杜椿虽然对洪枫还是没有多少好感,但刚听完他这一通长篇大论般的规划,他不得不承认,洪枫是有工匠精神的。同时,他也发现,他和洪枫之间的差距,就在对一件事情的专注和热情上。洪枫仿佛永远有一腔热血,朝着一个又一个目标前进,和父亲学木匠的时候是,开木器加工厂的时候是,现在张罗这个陈列馆也是。而他,被朝九晚五困住,被一份又一份材料困住,被数据、契约困住,复制粘贴般重复着一日又一日,已经很久没有特别想做一件事的冲动了。
杜椿有些惭愧,说:“这方面你是行家,规划得很好,一切你做主就好了,我也没什么想法,门外汉。”又怕他觉得自己说的是客气话,补充说,“我说的是真的。”
洪枫一迭连声说:“那就好,那就好。”
这时他们走进了工具间,和视频里看到的一样,墙上的工具错落有致插挂,屋子中央超大的工作台上,乱糟糟的都是板材、刨花、木屑、散落的工具,好像父亲正在忙,只是出去了一会,待会还要返回工作台。鲤鱼墨斗的班母也还吊在那儿,仿佛上一刻父亲正在拿它当吊锥测水平。杜椿拿起墨斗,抹了下鲤鱼身体上的灰尘,墨池里的墨早就干了,他小心地将墨线收回去。
“当年我还在你这个房间睡了好几年。”洪枫边感叹,边捡起桌上一张已经用过的砂纸,将工作台上的几缕刨花往地上刮。
工作台旁边还有一个倒装的电锯台,洪枫用手转动了一下电锯的转轮说:“师父的小拇指,是因为我才没的,要不是师父当时手快,被锯掉的,可能是我的左手。”
杜椿有些震惊,看着那个电锯的转轮说:“这个我真不知道,我爸没说过。”这件事别说杜椿了,可能连母亲都不知道。他只记得那时候父亲说是使用电锯时,不小心造成的,但没有说具体过程,更没有说和洪枫有关。想来是怕母亲埋怨洪枫吧?
洪枫那时主动提出并承担下张罗陈列馆的事,杜椿有过猜测,他图什么呢?现在他似乎有了答案,他可能是为了报恩吧,报父亲挽救了他的左手的恩,也报没有父亲,就没有他现在的事业的恩。
他沉吟了好一会了,因为他不知道该用什么反应去应对这件事。
最终,他还是走过去拍了拍洪枫的肩,没有说什么,不管父亲当年为什么没有说明是为了救洪枫才没了小拇指,现在的洪枫又是抱着什么心态去揽这些事的,他突然觉得没那么重要了,因为结果都不会改变。
看着有些被父亲使用过无数次的工具,木柄都包浆了似的泛着幽光,闻着工作间里淡淡的木材气味,他心里一动,脱口而出:“这里收拾一下,就当作木匠工具的陈列室,你看怎么样?”
洪枫从电锯上回过神来,看向杜椿:“这是个很好的主意,到时候给每个工具边贴上标签,介绍说明一下,除了木匠,估计没人能叫得全这些工具的名字。我就说,你读书多,能想出好点子。”说完,又补充道,“师父知道了,肯定很喜欢这个想法。”语调拔高了三分,带着欣喜。
杜椿与父亲最近的、也是最后一次冲突,与小楼和老屋有关。
那天,父亲突然打电话告诉杜椿,他想把那老屋和小楼整理一下,搞个木器陈列馆。在省城工作的杜椿,已经半年没回去了,虽然从省城到潜川,驱车只要一个半小时。接到父亲的电话,他第二天就请假回了一趟老家,他不知道父亲突然折腾什么,他有些懊恼自己没能早一些,至少在父亲开口之前说出自己的打算。杜椿有一个作家朋友,得知他老家有那么多闲置的房子,还有大片的桂花林,又在景区山脚下,闲置着太浪费了,于是提议和他一起搞民宿,就是靠他介绍的作家朋友来短租写作,生意也不会差。
推开老房子那扇虚掩的双开木门,杜椿喊了一声“爸”,在满屋子落满灰尘的木家具、农具的包围中寻找父亲的身影。那些残疾木器静静地看着他,默不作声。
父亲的声音从外面传来:“是椿儿回来了吗?”
出得门去,杜椿看到父亲站在小楼的二楼阳台上,好像又苍老了一些。杜椿这才意识到,租住在小楼里的人已经搬走了,他仰着头对父亲说:“房子都腾出来了,怎么没和我说一声,好歹这房子是我花钱盖的。”
父亲没有说话,转身消失在阳台的楼梯,杜椿想象得到瘦小微驼的父亲正不紧不慢地扶着栏杆下楼梯。院子一角放着一个少了一扇门的三门橱,一条因为脱榫而歪斜的长条凳,这是村里人拿过来的,父亲乐于为他们修理这些老物件,更确切地说,父亲愿意医治他所有生病的木器朋友。
父亲一边修那条板凳,一边将自己的想法告诉杜椿:“现在景区的游客量挺多的,在村里搞一个木器陈列馆,让那些城里人,还有小孩子们,认识一些快成为历史的农具,老式木家具,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换了一个横档,打了几个木楔后,父亲坐在长条凳上,微微摆动身体试了试凳子是否稳固,又指了指小楼:“把几间屋子中间的墙开个门,这四上四下,能放不少东西,”没等杜椿接话,“老屋再稍微整一下,也能放一些。本来想大修一下,现在看,老屋本身也很有看头,现在这种老屋子不好找了,村里几乎都没有了。”
杜椿想到自己的民宿,一心想要阻止:“你讲得轻巧,要花多少人力和财力,后续的事情更多,你一把年纪了,谁照看这个摊子。”
“我和洪枫商量过了,他很乐意帮我这个忙,他做事靠谱,也有能力。我盘算过了,手头的积蓄用来修房子什么的够了,屋里的家具农具修修还不够摆,样式也不全,但慢慢添置,不着急,先把摊子铺开。”
“这小楼我打算和朋友合伙搞民宿。”杜椿指了指小楼说。他想,这句话比“我不同意”更有反驳力。
“民宿是什么东西?”
“类似于旅馆,但也不是你想的那种旅馆……”
“在这里开旅馆,哪有生意?”
“没开怎么知道?”
“你不在家待不知道,景区就这么大,不是节假日根本没什么人来爬山,即使有人来,也都是本县或周边县的人,来回要不了3个小时,再爬个山,大半天足够,谁会住在这,钱多烧的啊?”
“你什么都不懂就瞎说,据说市里投了一大笔钱给这里,用于景区的周边建设,将来这里会大火的。现在人利用双休日出来放松放松,就喜欢来这种自然景点呼吸新鲜空气,这里客流会越来越多的,开个民宿,生意绝对好……”
“你赚那么多钱干吗?”父亲打断他。
杜椿被父亲呛得心底的火腾腾窜上来:“那你一大把年纪了,还学年轻人瞎折腾,吃饱了撑的。说民宿没人住,你那个什么陈列馆就有人……”他没有继续往下说,因为他发现父亲的脸色非常难看,眼神中充满了复杂的情绪,失望?惊恐?愤怒?他不好形容。
父亲没再和杜椿抬杠,将手中的斧头往工具箱里一扔,砸到刮铲和锉子,哐当一声脆响,起身走了。
后来,母亲和姐姐杜桂都当说客劝过杜椿,意思是父亲一生都离不开那些木器家伙了,现在老了,也做不动活了,他想搞那个什么木器陈列馆就让他搞吧。杜椿向来比较听母亲和杜桂的话,他退让了一步,但也有自己的坚持:“那就让他搞吧,但是别打我那小楼的主意,我已经答应朋友,再加盖一层,搞个民宿。”
后来,因为疫情原因,不管是杜椿的民宿,还是父亲的木器陈列馆,都没了下文,他们似乎都借着这个理由,等着对方先妥协。父亲还是在用实际行动告诉杜椿,他没有放弃,他开着自己的三轮车,像个收废品的,跑遍了周边乡村,淘来很多木器老物件。
叔叔杜楝来找杜椿的时候,杜椿和洪枫以及几个工人,正忙着安装院门的门楼。做红木雕刻,最重要的是眼睛,杜楝也老了,眼神不好使了,加上他家现在的条件优渥,几年前,他也就从苏州回来了,一直跟着儿子定居在省城。
“听说你在搞这个木器陈列馆,我回来看看。”叔叔说。
杜椿陪着叔叔四周逛了一圈,介绍了下陈列馆的情况。杜椿知道叔叔看到那些木器,心里也是很有触动的,因为可以从他在一些木器前停留的时间,以及抚摸那些木器的手势中看出来。
叔叔站在一个木桌前,说:“这个是我打的。”
“我一直都不是很会辨别这些木器出自谁的手中,这怎么看出来的?是这抽屉上的这个雕花吗?”杜椿拉开木桌的抽屉,又关上。
叔叔说:“不光是这个,你把抽屉抽出来,看看里面。”
杜椿抽出抽屉,弯下身子,将目光递进去,发现里面有一个暗格,他扒拉了一下暗格的推拉门,说:“这是用来藏家里值钱东西的吧?”
叔叔颇有些骄傲地说:“对啊。”
叔叔后来发现了好几样他曾经打制的家具,发出感叹:“我还以为你爸只会收集‘三杜’的东西呢!”
“怎么会呢?您手艺那么好。”杜椿说,他所了解的父亲也不是那样的人,木器在父亲眼中都是一样的,不会去分到底是谁打制了它,不然他也不会走村串巷收集来那么多不是出自杜家木匠手下的木器。
“怎么不会,他本来就看不起我啊,自从我去苏州后,他就更看不起了。当年,我邀请他去苏州,也是好心,你知道他怎么说的吗?”
杜椿看着叔叔,等待着他的后话。
“他说,钱我一个人挣就好了,他不能忘本,要守着村里,守着祖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得我好像是个叛徒,把杜家的木匠手艺丢了似的,就我见钱眼开,他有觉悟,他高尚。”
杜椿没有说什么,他知道这确实会是父亲说的话,但叔叔也过度解读了父亲的意思,这个时候,他不想和叔叔辩解什么,父亲都没有和叔叔说通的道理,他又怎么能说得通。
叔叔意识到自己这时候说这些不太合适,也立即错开话头:“算了,算了,不说了,都是陈芝麻烂谷子的事了。有什么我能帮得上忙的事情,你尽快说,我现在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父亲说得对,洪枫到底是一个做事靠谱的人,在他的满腔热情尽心尽力操持下,陈列馆很快就完工了,和他之前规划的一样,雕花的仿古飞檐门楼,六角亭,馆藏大大小小的木器物件有1800多件,其中不乏洪枫贡献出来的一些颇有收藏价值的老家具。
父亲的工作间基本保留了原样,连一些半成品的木器,解过的板材也都摆放在那里。只是墙上的工具参照之前的陈列方式,三面墙体上各增加了几排木条,工具分布更为稀疏均匀,每个工具下面都贴了一块标识牌,标明它叫什么,是属于采伐工具、解木工具、平木工具、测量工具还是雕刻工具,考虑到有小学生来看,甚至还注了拼音。
木工工作台中央,做了一个四方的玻璃罩子,里面有一个红木的浪花形底座,浪头上,站着重新上了清水漆,生机再现的鲤鱼墨斗。底座的标识牌上写着,划线工具:墨斗;制作人:杜松。
刚生二宝没多久的姐姐杜桂回来了,一直在县城照顾她的母亲也回来了,站在这个墨斗前,母亲噙着的眼泪,终于落了下来。
杜桂递过来一张纸巾,说:“妈,这大好日子,哭啥。”
母亲说:“高兴的,高兴的……”
开张的这天,除了村民和游客,镇里、村里以及景区的领导都来了,给予了肯定和表扬,说现如今已经实行了现代化,从以前的贫穷落后,到现在的繁荣富强,这个历程本身是记忆,也是文化,传承传统农业文化具有更要的意义,杜椿是在做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
杜椿也是在那一刻,非常明确地感受到父亲的良苦用心。
洪枫请来了县里的多家媒体,对陈列馆进行了宣传和报道。县电视台记者扛着摄像机拿着话筒要采访馆长的时候,杜椿推出了洪枫,洪枫却无论如何都不肯出镜。
洪枫后来说的一句话,让杜椿想到父亲那句关于木工工具的深奥名言。他对杜椿说:“我希望没能成为‘杜四’ 的你,能将“三杜”精神,将传统木器文化发扬光大。”
杜椿说:“在我爸心目中,你就是‘杜四’,我现在也觉得,你担得起这个名号。”
第二天,杜椿拍了很多陈列馆内内外外的照片,洗印了出来,洪枫备了酒菜,他们一起去往后山。山林飒飒,山顶寺庙里的梵音若有似无飘荡在耳畔,无数树木正在散发属于自己的气息,杜椿看着那些树,在心里一个个叫它们的名字,松树、杉树、榉树、栾树、野柿树、葛藤……
一座新坟前,两棵柏树静静地站立着,姿势端正,守着的似乎不仅仅是那座坟。
摆好贡品和碗筷,斟好酒,点燃一扎黄表纸,杜椿和洪枫将那几十张照片一张张投入火中。洪枫说:“师父,你交代给我们的任务完成了,你还满意吗?”火光在他的眼中跳跃,跳出了晶莹的光。六个月前,父亲突发脑溢血,倒在了工作间里,倒在了他付诸一生的热爱的木头身边。面对着病床上已经失去语言功能与思维的父亲,洪枫说:“师父,你放心吧。”那时候,他的眼中也有晶莹的光。
杜椿说:“爸,陈列馆免费对外开放,我请了叔叔照看,他是最合适的人选。”
火光舔舐着照片,舔舐着那些木器和农具,舔舐着鲤鱼墨斗,舔舐着六角亭,舔舐着气派的门楼上香椿木的牌匾上,叔叔杜楝雕刻的“三杜木器陈列馆”几个朱红大字。
相片迅速翻卷成灰烬,在灰烬之上,那些木器的轮廓影像依稀可辨,有风起,带着无数树木的香气,将灰烬吹散,锯末一样在父亲的坟头起舞。
(选自《安徽作家》2023年第2期)
作者简介

夏群,安徽庐江人,中国作协会员。作品见《小说月报·原创版》《雨花》《四川文学》《福建文学》《延河》《山东文学》《广州文艺》《边疆文学》等刊。出版中短篇小说集《荒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