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6-20 来源:安徽作家网 作者:安徽作家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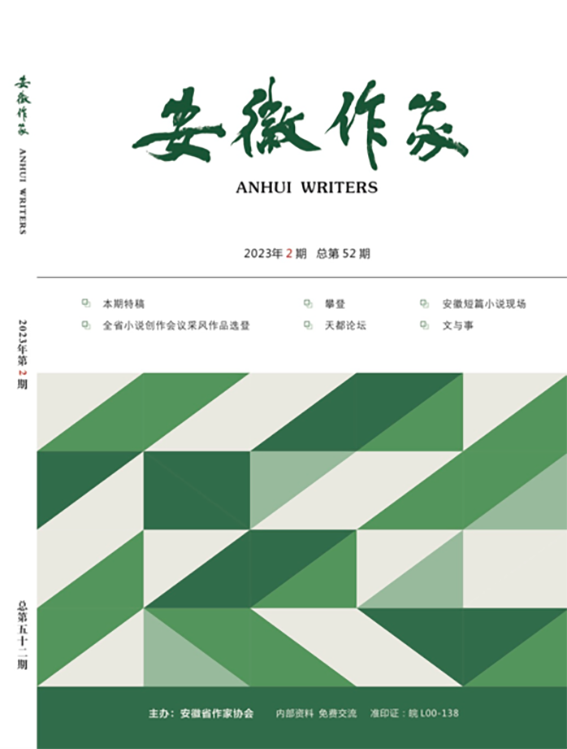
作品欣赏
春天里的舞影
朱斌峰
春天里的夜晚有神秘女子惊现而舞的消息,是彩山村村长打电话告诉我的。当时,我正在银城玻璃制品公司展厅里,领着一群衣冠楚楚的客人,观赏九层玻璃塔的模型。村长的声音从大山深处飘来,迟迟疑疑,像是被风吹得欲断还续的细线。我礼貌地掐断电话,心生烦躁。我早已不再关注新闻、八卦和流言——有人欢欣鼓舞地说这是伟大的信息时代,可在我眼里,那些纷纷扰扰的信息无非是不同面目的裁缝各取所需缝制的盛装,看似天衣无缝,其实破绽百出,甚至衣不遮体。我有个号称影视界大咖的朋友祥子,三杯酒下肚,就会激情洋溢地说起当红明星的秘闻,如同亲眼所见,其实只是在贩卖不知从哪儿听来的绯闻——不过那家伙摇晃大脑瓜的样儿,像是为大灯泡做广告,还是可亲可爱的。我不奢望从那些满天飞的泡沫里听到真相,只是耐心地保持着微笑,就像面对一堆碎玻璃发出的声儿——可村长的消息还是让我心里飞进了半只蜜蜂。
春天里不是季节的名称,而是一幢立在山谷里的房子。去年,我从彩山村村民手里买下两块宅基地,花了比制作微型玻璃塔还要长的时间,建起了那幢玻璃房。不大的山谷里只有它遗世独立着,钢木结构的三层楼,大面积的玻璃墙收集着山峦、云朵和星星的影子。山谷外的彩山村,徽派旧宅和水泥小楼错杂着,墙根下的木风车、田野里的稻秸垛、大树下坐着的戴草帽老人,显得空旷而寂寥。那幢玻璃房就像是从我心里长出来的,唯一遗憾的是,每逢雷雨天,房内的电闸就会被闪电吓得兀自跳开——据说源源不断的电流从城里抵达山谷就已微弱,只有插上两根水泥杆安上变压器,才能保持玻璃房灯火通明。我原本想把它建成民宿,可建成后就不愿对外开放了。我偶尔会独自或约上三五好友去那儿,跟山风、树林、飞鸟作伴,过几日不被打扰的时光。
有天晚上,我独坐在阳台上,看着天上的星星。手机里有人在唱《春天里》,不知是汪峰还是旭日阳刚。我听了一遍又一遍,听得眼睛都湿了,于是就把玻璃房命名为“春天里”。
我不愿意有陌生人走进春天里,即便那是个神秘的会跳舞的女人。
春天里的确住着一个女人——她叫梅姐,是个帮我打理玻璃房的五十多岁的胖妇人。
梅姐一直跟随着我,在春天里还没影儿时,她是银都玻璃制品公司的厨娘。我爱吃她烧的酸菜鱼,百吃不厌。更早之前,我还没出生时,她就跟她家的桃树以邻家姐姐的姿势,站在我家隔壁的院里。矿山家属区有着排列成行的平房群,像是被酒醉的诗人写乱了的诗行。我家所在的那行诗句里,住着九户人家,外墙都是红砖的,内墙刷着半截绿漆,每家每户格局相似,都摆放着木头茶几、五屉橱、黑白电视机什么的。夜半时分,矿区地皮轻轻颤动时,我就觉得自己正乘坐着一列绿皮火车,在大山里钻来钻去。矿山工人来自五湖四海,口音相杂,像是奔赴同一个目的地的旅客,可每个人的来路不同,什么金沙江、葫芦岛、枫香墩,那些陌生的地名让我好奇而又向往。梅姐的父亲来自四川,从部队转业到矿山大食堂当炊事员。他总把白毛巾搭在肩上,随时随地擦着脸上的汗。他爱摇晃着胖墩墩的身子,脸上漾开满足的笑,吹嘘他在部队是神枪手,吹嘘他老家有座石佛有大山那么高,吹嘘他的厨艺全矿第一,浑身得意劲儿仿佛矿上人都是他喂养的。梅姐却是安静的,她站在她家的桃树下,眼神像是被天上的小鸟叼走了。
每每吃晚饭时,梅姐会隔着竹篱笆,递给我一小碗酸菜鱼,像是给馋嘴的小猫喂食。
我吞下鱼片,仰着脸问她,梅姐,你长大后想做什么呀?
她甩甩长头发,能干什么?做矿工呗!我真想去银城,做纺织厂女工。
我嘻笑,大头哥说,纺织厂女工多,钢铁厂男工多,最好男去纺织厂女进钢铁厂。
她咬着米粒,为什么啊?
我盯着她好看的脸,物以稀为贵嘛……那样就好找对象了!
她的手指从竹篱笆穿过来,点在我的头上,你啊,真是人小鬼大!
其实,那时我们早就觉得有些事情是天生注定的,当南腔北调的父辈来到大山里建起矿山后,他们就坐上了同一列火车。作为他们的儿女,我们会子承父业把矿工进行到底,只不过男生大多下井采矿,女生可以去矿山广播站、幼儿园、地磅房、矿灯房而已。我们已经撇去父辈的方言,以同样的腔调说话,就像兄弟姐妹一样有着同样的命运了。我们晓得矿工是自豪的职业,却想去大山外的银城上班——虽然矿区有学校、粮站、邮电所、卫生院、供销社、工人俱乐部,足够让我们衣食无忧地完成娶妻生子、生老病死,却没有像银城那样的动物园。我们常常挤上运送矿石的小火车,在哦哦哦的汽笛中,在咔咔咔的微颤中,钻出大山去往并不远的小城,而纺织厂、冶炼厂、钢铁厂就是银城的标记。
我偶尔能听见梅姐在院子里轻轻哼着歌儿,跟芭蕾舞里的小天鹅似的转着圈儿,哼着转着,那棵桃树就开花了,她就长大了。
从矿山技校毕业后,梅姐果然去地磅房上班了。没过多久,她就有了男朋友。那家伙是矿山附近制药厂的销售员,高高大大,头发自然卷,腰上的钥匙串发出叮叮当当的金属声。据说他很有本事,制药厂的葡萄糖一半是他卖出去的。他第一次走进隔壁院落时,我就对他有着莫名的敌意,就像面对突然而至的闯入者。
我隔着竹篱笆,赌气似的对梅姐说,梅姐,我不喜欢卷毛哥!
梅姐有些意外,为什么呀?他有啥不好吗?
我闷声,反正就是不喜欢他!
梅姐咯咯地笑了。
梅姐嫁给卷毛哥后,常常坐在卷毛哥的摩托车后座上,风驰电掣地回来吃饭。卷毛哥能吹牛会喝酒,总跟梅叔喝得勾肩搭背亲如兄弟。梅姐就像偷食了梅叔的面包发酵粉幸福地胖了起来,连笑声都胖了。
就在梅姐生下女儿时,矿山因资源枯竭关停了,那真是出乎我们的意料,如同发生了一场火车脱轨侧翻事故。运矿小火车停开了,工人俱乐部听不见《咱们工人有力量》男声大合唱了,机关大楼楼顶大喇叭哑了,矿工们纷纷下岗出外寻生计了,人去楼空的矿区恍惚一下子就衰老了。梅姐下岗后,长头发剪成鸡窝状,整日抱着女儿在台球室里忙碌着,脸色蜡黄了。我在心里问自己,为什么梅姐不能像矿上的广播员——那个从北京来的单身阿姨那样,躲过时光的腐蚀,总保持着小姑娘的样子呢?
那时,我在银城东奔西突,先开了玻璃店,为小城千家万户切割玻璃门窗、安装玻璃阳台,然后又在开发区的田野上拿下一块地,建起玻璃制品厂,生产盛装化妆品、药品、酒水的器皿。等稍稍能喘口气时,我回到矿区,才发现梅姐正在破败的街道上枯萎着。卷发哥跟一个长发女人好上了,梅姐跟那女人明争暗斗后离婚了,正带着女儿靠着台球室过生活。她灰头灰脸,整日神情慌张,脸上像是锈住了。她还患上了一个毛病,一看见女人的长发就会心悸眩晕发偏头痛,那应该是婚姻事故留下的后遗症。于是,我将梅姐母女接到银都玻璃制品厂。她不愿意跟玻璃打交道,就一直在厂里做厨娘,烧的酸菜鱼还是当年的味道。
这样的梅姐真没什么神秘的。
我不相信春天里有人夜半而舞,可传言还是像无微不至的风来了。
我想我应该去彩山村堵住村长的嘴,让那流言不要传开。我开着车捎着朋友祥子,从银城向大山驶去,不是去春天里,而是去拜访村长。我想了许久,也没想出村长向我透露传闻有何居心,只是想起他曾热情地陪我逛过整个村子。他指点着村里的旧祠堂、半山的寺庙、远处的鸡鸣驿和空置的徽派旧宅,说起当地的掌故,谈起他想把彩山村建成影视拍摄基地的计划,并恳请城里大老板的我为他出谋划策牵线搭桥,当时我满口应承了——也许村长是在提醒和催促我吧。我邀请祥子同行,就是想让他以影视界资深人士的身份,考察考察彩山村,给村长一个交待。我甚至想,如若村长肯缄口不语,我愿意为美好乡村建设制作一个应景的玻璃雕塑。我在车上把事儿跟祥子说了,祥子摸着被安全带勒紧的肚子,弥勒佛般眉飞色舞起来。
这算啥事?你一个大老板,怎么还为这种小事叽叽歪歪?
我呵呵地笑。
其实咱俩挺有缘的……我以前在国营灯泡厂干过……吹过玻璃灯泡儿。
哦?
那时,咱们厂长牛皮哄哄,整天说要造出人造小太阳!
人造小太阳?
就是那种一千瓦的氙气灯……厂长想用那种大灯泡照亮光明路整条街。
那厂长的计划成功了吗?
没有!咱们是狗咬猪尿泡空热情了一场……当年咱们真是年轻啊!
后来呢?
后来,灯泡厂被厂长买断成了私营企业,专门生产霓虹灯了。
……
我不知道祥子的故事是他亲身的经历,还是他习惯性的虚构,也许连他自己都分不清真假。我很佩服祥子能把每一个故事,说得生龙活现,说得津津有味。我在建成玻璃制品厂时,也曾有过生产玻璃灯饰的想法,连名字都想好了——三色照明公司。可我只会收集液体,不会收集光,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在银都广场上建起高耸的九层玻璃塔,与小城铜质钟楼、木构鼓楼遥相呼应。
山路越来越窄越弯曲,植被越来越多越充沛。我们渐渐把喧嚣抛在身后,遁入静静的时光。我们钻到彩山村时,村长已经在村部门口迎候了。大山被湿湿的绿浸润着,山顶萦绕着白白的雾气,天上的云里似乎藏着一场细细的雨水。我们跟着村长走走停停,那个外表墩实的中年男人把村里的掌故又讲了一遍,说得那么熟稔,就像吐着一根被日光暴晒过的稻草。我听得恹恹欲睡,只是意外地发现村头晒稻场多了个名叫彩山人家的小型民俗博物馆。那石基土墙的大院里,摆放着水缸石磨、风车犁铧、织布机绣花鞋、木制摇篮和铜锁扣上的木柜之类的器物,在昏黄的光线里弥漫着遥远的告别气息。祥子发出夸张的笑声,不停地用手机取景拍照,似乎想把那些老物件收进手机里。我知道要不了多久,我的朋友会在朋友圈里,以九宫格长篇累牍地推出做旧了的照片,引得点赞如蜜蜂般嗡嗡飞起。
等我们在村部坐下,偌大的会议室里只有祥子洪亮的声音了。那个大嗓门的家伙滔滔不绝地说起影视圈见闻,高屋建瓴地谈起彩山村打造影视基地的策略,信誓旦旦地说他可以引进他的朋友执导的《山乡巨变》剧组走进彩山村。他的话就像泥石流冲刷而来,村长插不上嘴却蠢蠢欲动着,不停地斟茶递烟点头称好。我知道祥子的话满是水分,听着听着却忍不住激动起来,既然乔家大院、宏村染坊能凭着一部影视剧火起来,那彩山村未必不能如祥子所说声名鹊起的。一阵风从窗外吹来,我倏地冷醒过来,为自己刚才的激动羞愧。其实,我并不想彩山村被人打扰,可那些激动人心的话让我中蛊了——也许我们都是叫不醒的做梦人。
奇怪的是,村长一直没有提春天里有人跳舞的事儿,那让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幻听了——作为曾被玻璃的尖嘴刺伤过耳朵的人,偶尔幻听是不无可能的。可等我们坐进乡村土菜馆,喝得耳酣面热的村长竟然开口了。他说好多村人都看见过,午夜的玻璃房阳台上,有个长发女子穿着白色衣裙跳起舞来,待细看时又不见了。我虽然早有心理准备,可仍听得心惊肉跳,仿佛那是个不祥之兆。
我喃喃,怎么会?怎么可能有这种事?
村长笃定地看着我,怎么说呢?咱们这儿有个传说……听说很久很久以前,彩山上就有白云变成女子在山顶上跳舞……咱们的先人就是看见那个异象,才在这儿定居下来开花散枝的。
我心稍安,这个传说听起来还算吉利。
村长的脸被酒泡得模糊了。后来就总有人看见白衣女人跳舞……就说四十年前吧,一个从上海下放到村里小学教书的女子跳下悬崖后,又有人看见白衣女子在山上跳舞……没想到这事儿又在您的玻璃房出现了……
我的心又被揪了一下,嘴上浮出笑,怎么会?不科学嘛!无稽之谈!
村长连声应,对对!就是个无根无据的传说!
一串笑声泼染开来,祥子腆着大肚子眉开眼笑了,这是好事啊!不管这事是有是无,只要传开来就能吸引人来……有些景区不就是编造这样的噱头吸引人气么?看来这里就要成为网红打卡地了!
我和村长怔怔地看着祥子那张过于肥大的脸,都没说出话来。
我恍惚听见春天里满山谷的鸟雀聒噪起来。
关于春天里的传闻,就跟龙卷风般流传开了。
先是祥子发了朋友圈,绘声绘色地说起彩山村一个玻璃房里疑似出现了灵异事件,还配发了一张嫦娥奔月的图片。接着,好几个熟识的朋友打来电话,或开玩笑或神叨叨地向我查证传闻的真伪。我矢口否认,却让他们更信以为真了。再后来,传言在网络上传开,不时有陌生人打电话给我,说要入住春天里民宿,气得我差点换手机卡了。果然,流言比瘟疫还有传染性,比风跑得还要快。我讨厌流言蜚语的灰尘,却不怨祥子,他真正的身份是小城作家,就是靠贩卖浮光掠影的故事为生的——至少他比那些拼贴新闻贩卖消息的媒体工作者要有趣。我没答理这事儿,不信一条虚假的小鱼能翻起浪花。我想要不了多久,这条传闻就会被更多的泡沫淹没,就会烟消云散。
事情总是出人意料:竟然有人根据流言判断我在春天里金屋藏娇了,怀疑跳舞的长发女子是我的情人。她是睡在我身边的女人,眉毛画得很细,眉峰画得很高,很重的眼影遮不住眼角的皱纹,脸部就跟悬崖峭壁似的。她没有跟我争吵,在我面前总是冷着脸专心致志地涂着脚指甲,私下里却派人在玻璃房前蹲守,仿佛那条流言变成锈迹斑斑的钉子扎进她心里了。我想跟她解释什么,却不知怎样开口,又不敢把事儿越描越黑。我宁愿她在春天里捉到跳舞的女人,是聊斋里的狐狸也好,是我的情人也罢,那样她悬着的心也许会踏实下来。我甚至想雇一个长发女人去玻璃房跳上一曲午夜的孔雀舞,了却她的心愿。
我更没想到春天里因传言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梅姐急急地打来电话说,她发现一到夜晚就会有好多眼睛甚至摄像机镜头对着玻璃房,让她提心吊胆,像是囚在大探照灯下的监房里——这真是让人不愉快的感觉,城里已经有足够多的电子眼了,为什么大山里还要有复眼动物呢?我思来想去,不便派保安去守护玻璃房,只好单身赴会去往春天里。
这天晚上,我吃过酸菜鱼,与梅姐坐在玻璃房阳台上,喝着咖啡闲聊。晚霞逐渐散去,天空和玻璃墙显出纯净的暗蓝,山谷里的树林在风中轻轻摇摆。
我问梅姐,你看见过有女子穿着白衣,在阳台上跳舞吗?
她摇摇头,斑白的短发像被秋霜打过。
我又问,那你相信那个传闻吗?
她还是摇头。
我轻轻地笑,那你怕什么?
她抬起眼,慌慌地扫了扫四周的树林,我不怕鬼怪,就怕人的眼睛。
我看见她哆嗦了一下,便低下声,梅姐,别怕!没什么可怕的!
她定定地看着我,点了点头。
我俩又说起矿山往事,聊起她远在北方上大学的女儿,断断续续的声音跟山风融在了一起。渐渐,那种久远的好看的笑,从她的脸上漫了出来。
等星星出来偷听时,我俩各自回卧室了。不知梅姐有没有安然入睡,而我在静等着午夜的到来。我一遍遍地摩挲强光手电筒和一把角铁制成的刀,那不是为可能出现的白衣女子准备的,而是用来对付那些窥视玻璃房的眼睛们。我要看看那是些什么样的人,必要时将刀插入他们的臀部。我从小就明白刀是雕琢事物最干净利索的器具——我曾用那把刀吓跑过少年时的情敌,讨要过玻璃工程款——只是那把刀有些生锈了。我对自己用刀的准确性充满自信,懂得如何把刀恰如其分地插入人体部位。我要重拾旧刀,制造一桩流血事件,把那些眼睛从春天里赶走。
当指针指向午夜十二点时,我拎着强光手电筒和刀,踅出玻璃房,钻进树林里搜索起来。几道强光暴射之后,传出几声惊呼,然后强光和惊叫就被黑色吞没了。我绕着山谷走了一圈,看到了九张被强光手电筒照射得骤然变形的面孔。有六个陌生人自称是喜欢探险的驴友、直播爱好者和新闻从业人,那些叶公好龙、鹦鹉学舌的家伙胆子真小,被我吓得丢下一台小DV和半截手指落荒而逃了。
还有三人是熟人,我不得不把他们请进玻璃房里。
我盯着一张熟脸,你是村长,怎么也在这里蹲守呢?
村长抹抹头上的汗,舌头打结,那个……你别误会,我只是想搞好平安乡村建设哦。
我又转向另一张脸,祥兄,你呢?
祥子腆着坦坦荡荡的肚子,我嘛,就是想亲身体验一下,创作一部《午夜惊魂》之类的电影!
我笑笑,看向旁边抖抖索索的人,那个高颧骨的年轻男人仍闭着眼,像是被强光手电筒照瞎了。我没问他什么,他就是被人派来捕捉我的情人的人。
梅姐没有走出她的卧室,也许她睡得太熟,没有什么能惊醒她。
梅姐是自愿来春天里的。她说她总失眠,就想找一个安安静静的地儿,也许那样就能睡好觉。我起初不同意,担心她一个人在山谷里太孤单太不安全,准备找个当地村妇打理玻璃房。她就一连几天都不烧酸菜鱼,执拗地表示她生气了。我只好答应下来,真希望山谷里的风、云和星星能治好她的偏头痛。
梅姐第一次偏头痛发作,可能是在警车带走我的那天黄昏。之前的某个夜晚,刚上矿山技校的我和三个小伙伴,去银城翻进钢铁厂仓库拿了些角铁,用技校实训车床制成刀的形状,又跟冶金技校的学生打了一架,用那角铁制成的刀刺破了冶炼厂子弟的大腿,于是公安就找来了。他们开着警车奔来,把我们从矿山技校里揪了出来,游街示众般带着我们缓缓驶过矿区,以威慑我们的同类。当警灯闪烁的警车呜啦啦地驶向地磅房时,我把脸贴在车窗上,看见了站在青砖地磅房前的梅姐。她看见我,捂着嘴尖叫一声,愣了愣,就边喊着我的小名边跟着警车跑起来。她跑着跑着,脚步飘摇,忽地捂着脑瓜坐在柏油马路上——后来我才知道她犯了偏头痛。我起初以为是警车的叫声让梅姐落下病根的,后来发现自己冤枉了公安——在我认识的公安朋友中也有患偏头痛的——也许有些人就像天生洁癖一样,对某种声音过于敏感吧。我从看守所放出后,被父亲暴打一顿,在家里关了一个多月。我蜗在天昏地暗的家里,耳朵变得越来越灵,一听见隔壁传来小鹿般的脚步声,就走到竹篱笆前,对着下班归来的梅姐笑。梅姐会停下脚步,甩甩长头发跟我说说话儿。她不无忧虑地说,你啊你,这样混下去,矿里是不会收你当工人的,你长大后怎么办呀?我只能摸摸发青的头皮暗自气馁,脸上却坚持着嘻笑。那时工人是光荣的职业,而不能成为国家正式工、集体工就是盲流——现在想来,梅姐的担忧是多余的。
我第二次看见梅姐犯偏头痛,是在矿区工人俱乐部前。那天早晨,街上飘着淡淡的雾气。卷毛哥像一粒台球从台球室里滚出,骑上摩托捎着长发女子扬长而去。梅姐从台球室里冲出,看着摩托长发飘飘而去,瘫倒在水泥地上号啕起来。我上前去扶她,发现她像是散了骨架,怎么也扶不起来。雾气越来越淡,围观的矿工家属渐渐多了。我情急之下,背起梅姐一溜烟地跑回家。梅姐的偏头痛严重地发作了,痛得出现了幻觉,说她看见长发在她眼前飘来飘去,要我把那长发快快剪掉。我找到剪刀却找不到长发,心知那旗帜般的长发已被摩托带走了。梅姐悲泣地诉说着,说她失去了工作又失去了丈夫,真是命苦。梅叔叉着腰气汹汹地对着空气骂,说他要是有枪就一枪毙了卷毛狗。梅婶唉声叹气,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女儿怎么嫁了个吃喝嫖赌的男人呢!我没有说话,转身回卧室用砂纸磨打起角铁制成的刀。
一天晚上,我在迪斯科舞厅找到卷毛哥。那时,他从制药厂停薪留职,下海办了那家黑灯瞎火的舞厅。我对舞厅并不陌生,知道那里无非有一些男女在幽暗的灯光下,借着跳交谊舞的幌子,搂搂抱抱摸摸捏捏而已——我曾在那儿的地板上踩到过已经使用过的避孕套。我也曾在舞厅经理室,独自翻看过卷毛哥偷偷从香港弄来的《龙虎豹》,那画报上的裸女让我热血沸腾。
我一走进舞厅经理室,卷毛哥就笑着迎过来,像往常一样拍拍我的头,小弟,你咋来了?
我盯着他,梅姐那么好,你为什么还搞外遇?
他脸上肌肉僵了僵,声音是软的,这个……你还小,不懂。
我冷笑,懂你妈!说着刀就跳了出来,插在他的大腿上。
他痛呼一声,趔趄地跌坐在沙发上。
门被嘭地撞开,一个看场子的光头冲进来抓住我,对着卷毛哥喊,老大,你没事吧?是做了这小子,还是把他交给公安?
卷毛哥挤着眉头,挥挥手:放他走。
光头愣了愣,手慢慢松开了。
卷毛哥看着我,小弟……那种事,长大后你就懂了……你走吧。
我犟犟脖子,上前捡起刀,狠狠地盯了他一眼转身而去。
很多年后,我偶遇早已成为电子厂门卫的卷毛哥,想上前握握他的手却忍住了。我说:卷毛哥,作为男人我懂你了,可我不能原谅你!卷毛哥讷讷,唔,为啥?我笑笑,有时我连自己都不能原谅!卷毛哥没再说什么,像个陌生人转过身子。我眼睛有些潮,发现曾经高大帅气的卷毛哥过早地佝偻了。
梅姐的偏头痛最后一次严重发作,可能是在听到梅叔亡故的那天。那时,她正在银都玻璃制品公司食堂烧酸菜鱼,鼓捣起腾腾的热气。一个电话打来,有人告知她梅叔在乡村到矿区的路上,掉进河里淹死了。没了矿山大食堂,日渐衰老的梅叔偶尔会去矿区四周的乡村,为村里人家红白喜事帮帮厨,然后红光满面地骑着自行车回家。他老人家应该是喝酒喝多了,骑车栽进那条矿山排污河里的。我闻讯赶到食堂,看见一只翻盖手机断了翅膀似的扔在一边。梅姐正抱着头蜷缩在地上,在喊,痛!痛!痛啊——而酸菜鱼的香气正在四处弥漫。
其实,我对春天里能养好梅姐与生俱来的暗疾,是没有信心的。
春天里午夜舞女的传闻,就这样没造成实质性影响,泡沫般消散了。
有个朋友曾推着鼻梁上的深度眼镜,忧心忡忡地劝诫我,这是现象即本质的时代,传闻会变成真相。你必须消除那个流言,否则那流言传久了就会成为事实。我觉得他的话是呓语,可还是心悸了许久。当春天里恢复平静后,我在心里窃笑眼镜朋友,无论什么时代,谎言都不会变成金条——人想得太多就会生病哦。我刚放下心来,祥子打来电话,压低大嗓门神秘兮兮地说,春天里的舞女,只会在月圆之夜出现。我一笑置之,没把这话往心里去。我很忙,得在银城人模狗样地活着,要用玻璃吹制漂亮的器皿,甚至制造透明的玻璃塔——春天里的玻璃房只是我的偷闲处而已。
天近中秋,月亮圆了起来。我想起自己好久没去春天里了,就开着车迎着黄昏的落日,甩掉银城向大山驶去。一幢幢高楼的玻璃幕墙退去,一座座青深的山峦围来,我恍惚钻进时光的隧道。车至彩山村,我忽然想起祥子的话,心里一动闪出个念头:月圆之夜,玻璃房的阳台上究竟会不会出现白衣舞女呢?于是,我停下车在乡村土菜馆吃过晚饭后,悄手悄脚地攀上山谷里的石岩,眺望起玻璃房。身边的树木野草青润欲滴,仿佛叮叮咚咚的泉水就是从那些树根叶脉里流出来的。山顶薄云濡上微湿的青色,渐渐跟月光融成一片。对面玻璃房里,灯火不知何时亮起,又不知何时熄去,只留下阳台上那盏明晃晃的大灯。我没有看见梅姐的身影,只看见月光在玻璃墙上无声地纷落。
我左顾右盼,等着午夜的降临。我早已经历过一次次焦急的等待,可这次却有着悠然的清闲,就像把自己泡进了慢放的时光里。我恍惚听见草丛里的虫鸣、树叶的呼吸,看到夜气下植物在悄悄枯荣,感到一缕缕凉意沿着大腿游了上来。
月亮升上山巅,果然又圆又亮。忽而,对面玻璃房的大灯骤然雪亮,我睁大眼睛,真的看见一个白衣女子出现在阳台上,甩动长发跳起舞来。她仰着脸看着圆月,双手上举,脚尖踮起在悠悠转动,就像抓住长发要向月亮飘去。我用力揉揉眼睛,就在那女子转过身时,惊讶地发现那张脸是属于梅姐的。她的脸被月光照得很白很白,白得没有一丝皱纹。我在心里深深地喊了声梅姐,却不敢惊动她,悄悄转身踅出山谷,在山下启动汽车悄无声息地驶上月光的轨道。
春天里渐渐远去,我确定自己没有喝酒,也没有产生幻觉。我在心里问自己,我怎么从没发现梅姐喜欢跳舞啊?梅姐的短发怎么会变成长发呢?难道她买了头套?难道是我看花了眼?
车至银城,我才打开车载音乐,一首歌像料峭的风扑面而来:如果有一天 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 在那时光里/如果有一天 我悄然离去/请把我埋在 这春天里——
我想我该为春天里种上一树桃花了。
作者简介

朱斌峰,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中青年作家高研班第32届学员,安徽文学院第四届签约作家。曾于《钟山》《青年文学》《安徽文学》《西湖》《雨花》《青春》《天涯》《山花》《黄河文学》等发表小说,被《中篇小说选刊》《长江文艺·好小说选刊》《作品与争鸣》选载。获2015年《安徽文学》年度文学奖小说奖、第二届鲁彦周文学奖提名(优秀)奖,参与编剧的广播剧获全国第十二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