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6-26 来源:安徽作家网 作者:安徽作家网
近期,我省作家储劲松新著《在江湖与庙堂之间——贬谪中的宋代文人》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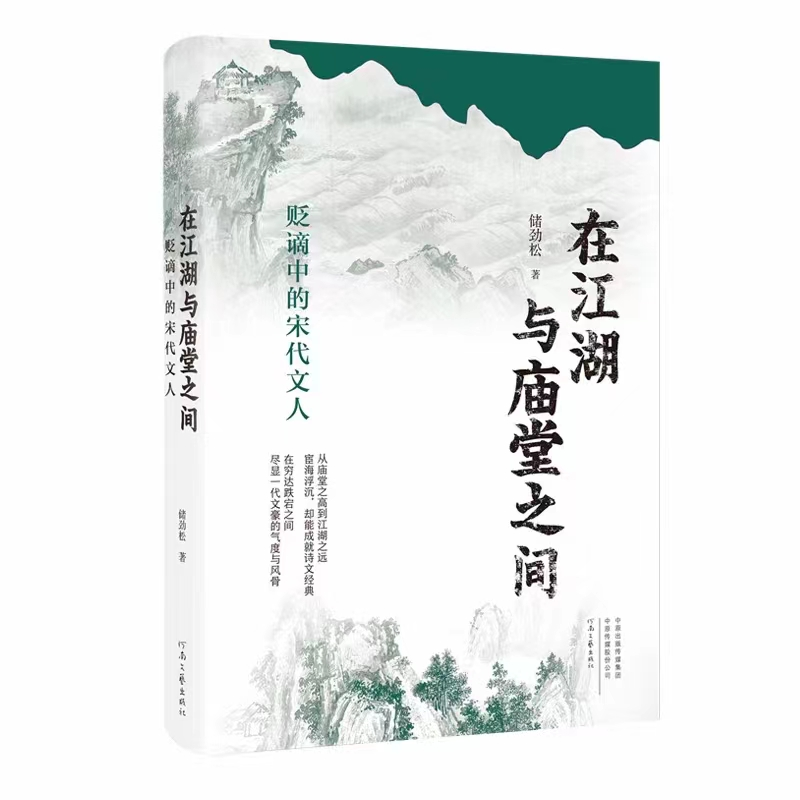
人生的得意失意,都是一代文豪的精神徽章。在这本书里,作家储劲松以两宋历史为背景,以青史、年谱、作家作品、传记、行状、祭文、墓志、历代相关文章等为依据,参以己意,以洗炼、劲健、朴厚之笔,集中重述了宋代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苏舜钦、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秦观、陆游、杨万里、辛弃疾等11位大文人,在贬谪或罢职期间的真实脚踪与心迹。
在江湖与庙堂之间——贬谪中的宋代文人(节选)
睦州在今天的浙江省建德、淳安、桐庐一带。范仲淹携一家十口,乘船由北往南,沿颖水、淮河而下,入富春江,历尽风涛险恶,于三月中旬到达桐庐,四月抵州治建德。途中作《出守桐庐道中十绝》,其一云:“陇上带经人,金门齿谏臣。雷霆日有犯,始可报君亲。”其七云:“万钟谁不慕,意气满堂金。必若枉此道,伤哉非素心。”由这组诗可知,当时范仲淹的逐客心态是很复杂的,但大体上落实在“素心”二字。所谓素心,就是儒家尊崇的道,就是初心。
素心无瑕,纯白如圭。
范仲淹抵达桐庐后的第一件事,是依例给仁宗上谢表。一番真真假假的客套言辞之后,他用了一大段文字,重述对废黜郭皇后的反对意见,并以历史上汉武帝废黜陈皇后立卫子夫、魏文帝杀甄皇后立郭妃、唐高宗废黜王皇后立武昭仪等为例,说明轻易废立皇后,极有可能导致后院起火,甚至导致江山板荡,再次劝说仁宗收回成命。谏语谔谔,奈何无益。
其《谪守睦州作》说:“重父必重母,正邦先正家。一心回主意,十口向天涯。”前两句,暗含规劝仁宗之语:君为父,后为母,正邦国必先正后宫。后两句,则是自己心曲的表露:他的谏诤,上为君主,下为黎民,哪怕窜逐远方也不悔恨。
多年以后的庆历六年(1046),范仲淹在邓州,应贬谪岳州的同年好友滕宗谅(字子京)之约,为重修岳阳楼作记,文章中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又说,“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他先忧后乐的“古仁人之心”,来自儒家经典,并且一生始终不渝地践行。
君子之道,如阳春白日,照临苍生。
睦州在浙西,为江左偏州,离京师有千里之遥,境内有富春江、分水江、富春山、桐君山、乌龙山、严子陵钓台、方干处士旧居、承天寺等风景名胜和文化古迹。
古代人口稀少,交通不便,除了京师所在地和边防重地,一般州郡的事务本就不多,主要是征收赋税、分配徭役和维持地方稳定。右文轻武的北宋更是如此,边远州郡的长官是闲差事。以范仲淹允文允武的大才,治理一个小州无异于牛刀宰鸡。当时,两浙民风轻躁而不刚。范仲淹治理睦州,对州中豪横如虎者,以文化之,对弱小的闾阎百姓,则多方拯济。一文一仁,不久睦州大治。
通与塞,擢与贬,达与穷,于凡庸之辈,无不喜前者而厌后者。但心怀天下的仁人志士,在逆境也能履险如夷,淡然处之。
范仲淹刚到睦州,就爱上了这里的山川风土。他在给恩师晏殊的书简中说,睦州满目奇胜,渔钓相望,群峰四来,翠盈轩窗,同僚中有章、阮两位擅文章、能弹琴的雅人,林中僧人乡间野客也往往上门来讨论诗歌,门生在这里作知州,大得隐者逍遥之乐。又半真半假地说,自己生怕有一天蒙恩被调离。在给其他友朋的信中,他一再说,睦州江山清绝,明丽照人,风月有旧,使人愉然。《与曹都官书》:“大为拙者之福。”《与谏院郭舍人书》:“曾不知通塞之如何。”《与王状元书》:“某四月半到郡,重江乱山,目不可际……而水石琴书,日有雅味,时得佳客,相与咏歌。”又在《和章岷从事斗茶歌》中说:“不如仙山一啜好,泠然便欲乘风飞。”
公务之暇,范仲淹或研读《周易》,或援琴写怀,或者与同僚和当地雅士遍览州内的奇山胜水,写了不少诗歌文章,如《新定感兴五首》《游乌龙山寺》《江干闲望》《斋中偶书》《和章岷推官同登承天寺竹阁》等等,多是自抒闲怀之作。
他在睦州写的诗歌,最有名的是《潇洒桐庐郡十绝》。这十首诗的第一句,都以“潇洒桐庐郡”起首。潇洒的,既是山川,也是他这个知州。诗中说:“劳生一何幸,日日面青山。”“人生安乐处,谁复问千钟。”又说:“相呼采莲去,笑上木兰舟。”“使君无一事,心共白云空。”细细品来,全然是遁世无闷之语,其清逸、喜乐自内心天然生发,较之后来欧阳修在滁州写的《醉翁亭记》,更无一丝造作。
范仲淹在睦州所作文章,以《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为第一。这篇文章和《岳阳楼记》,是范仲淹文章的代表作。范仲淹传世作品,文章之外,诗以《江上渔者》《河朔吟》为代表,词以《渔家傲·秋思》《苏幕遮·怀旧》为代表,政论以《上执政书》《答手诏条陈十事》为代表,另外还有为数众多的赋、义、论、议、赞、颂、述、序、跋、牒、祭文、墓志铭、表、状、奏、札子、书简、榜约……文学成就可谓晖映日月。范促淹是北宋继王禹偁之后的第二代文坛盟主,但客观而言,在大文人层出不穷的北宋,与欧阳修、苏轼、梅尧臣、尹洙、苏舜钦、黄庭坚诸人相比,其成就到底还是逊色一些。清人蔡铸在《蔡氏古文评注补正全集》中说,范仲淹“不以文章见长,而文章自堪千古,所谓有德者必有言也。”这话初看,像是冒犯,其实是很高的评价。明代周孔教为万历本范仲淹文集作序,说范仲淹的文名为功德所掩盖,流传天下的只有《岳阳楼记》和《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二篇。确乎如此。时至今日,现代人所熟知的范仲淹文章,则只剩下《岳阳楼记》一篇了,还是教科书的功劳。
对于胸有开物成务之略、怀有安邦定国之志的范仲淹来说,文学、书法和琴艺之类,只是余事、闲事、末事。出仕以来,他从没想过要以诗文名世。他认为,诗歌文章是明道、载道、贯道之器,所以从不为诗而诗、为文而文、为书而书、为琴而琴,更不刻意经营。他还在家书中,劝戒子弟不要迷恋书法,以免把自己的志向养小了,虽然他的书法端雅沉着,深得晋人笔意,倍受晏殊、杜衍、蔡襄、黄庭坚、王世贞等人称道。因从不刻意,其文章自然工巧。范仲淹文章之妙,由这篇祠堂记可知,实在是“圣贤经济”与“才子文章”兼得之。正如元代耶律楚材所言:“夫文章,以气为主,浩然之气养于胸中,发为文章,不期文而文有余矣。古之君子,其文见于简策,宏深浑厚,言近而旨远,辞约而义深,非后世以雕篆为工者所能比,盖其浩然之气贯于中也。”北宋文坛公认的盟主,首先是王禹偁,接着是范仲淹,后来是欧阳修,再后来是苏轼,四位“文章丈人”的盟主之名岂是浪得的?
睦州文化古迹,以桐庐严子陵钓台为最。严子陵名严光,是东汉著名隐士,《后汉书·严光传》所谓“有一男子,披羊裘钓泽中。”他与汉光武帝刘秀是同窗也是好友。刘秀开创东汉,握赤符,穿龙袍,仍然不忘这个少年知己,曾多次派人专程到严光隐居的富春山看望他,并恳请他出山做官,帮助自己治理天下。严光被逼无奈,到过洛阳一次,刘秀与他像从前一样睡在一张床上,半夜,严光故意把脚放到刘秀的肚子上,留下“客星犯帝座”的著名典故。刘秀请他做谏议大夫,他不肯,执意回到富春山麓,以耕读垂钓为乐。他垂钓的地方,原名七里濑,后来称作严陵濑,他垂钓的大石头,称严子陵钓台。
时间过去了一千年,范仲淹来此地作知州,景慕严子陵为人,在钓台下专门建了一座严子陵祠堂,并亲自写了祠堂记。不足三百字的《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文情峻丽,淳重清劲,浩然正大,我以为是范仲淹文学成就之集大成者,虽然远不如后来的《岳阳楼记》有名。就像苏轼赤壁二赋,固然是上佳之作,我以为其神采和意味,不如他那篇只有百来字的《记承天寺夜游》。
范仲淹在祠堂记中说:“盖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器,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哉!”在无数文人墨客吟咏刘秀与严光的诗词文章中,他独发卓见。末了,他高度评价严光:“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每每读这十六个字,我总在想,它们恰恰也是范仲淹一生的传神写照,比富弼、韩琦、苏轼、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张方平、朱熹等人对范仲淹道德、政绩、经术、文章的评价,更为契合。刘秀与严光少年时“相尚以道”,隔着一千年的漫长光阴,范仲淹引前贤严光为知音,也有“相尚以道”的意思。或许,在当时的逆境中,他也是以严光后身自许的。

储劲松,安徽岳西人,中国作协会员,现为安庆市作家协会主席、岳西县文联主席。作品发表于《中国作家》《青年文学》《长篇小说选刊》《天涯》《山花》《雨花》《广州文艺》《散文》《散文海外版》《散文选刊(选刊版》等刊物。著有《雪夜闲书》《草木朴素》《黑夜笔记》《书鱼记:漫谈中国志怪小说•野史与其他》等作品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