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4-04-10 来源:安徽作家网 作者:安徽作家网
近期,我省作家时国金佳作频发:散文《菊黄蟹肥忆圩乡》发表于《雨花》2024年第2期;散文《隔着时光的芬芳》发表于《绿洲》2024年第1 期;散文《月光、鱼和圩乡的水》发表于《山东文学》2024年第4期;散文《走近红旗渠》入选《人民日报2023年散文精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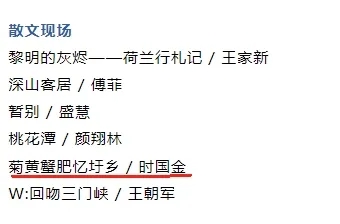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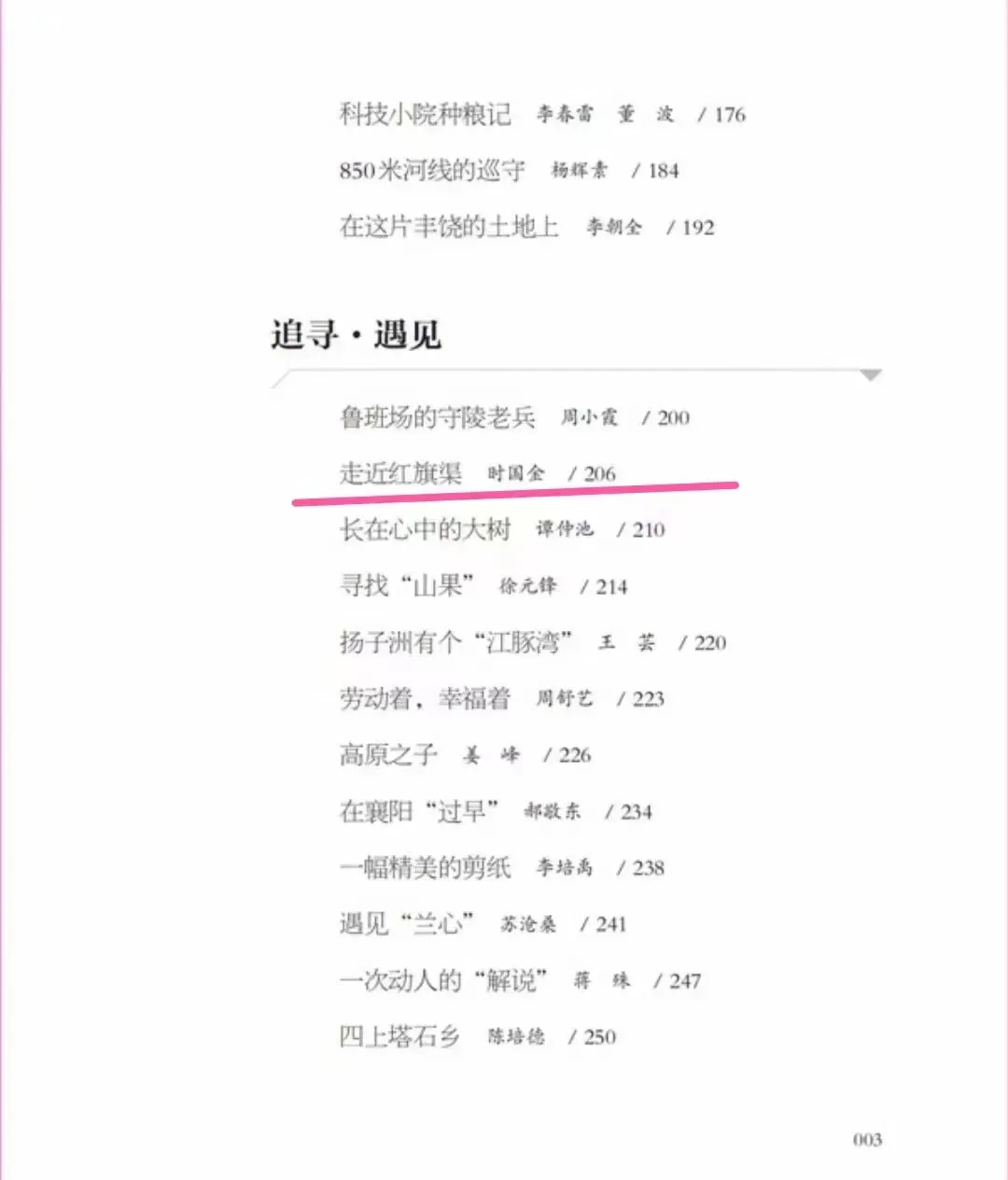
作品欣赏
月光、鱼和圩乡的水
时国金
曾经,圩乡的水和天是连在一起的。岸边,或船上,低头见天,一朵朵白云在水底飘荡,一条条小鱼就在云上漂游。深邃的天空中,飞翔的小鸟仿佛掬水可触。
水中的小鱼当然伸手能捉,并不怕人,水挑上有许多鱼。你若赤脚站在水挑上,它们会一群群地啃咬着你的脚趾和小腿,痒呼呼。这种鱼要么是痴呆呆的桃痴,要么是调皮的小鳑鲏。俯下身子去抓一把,抓到的大多是一片麻溜溜的鱼籽,粘乎乎地紧敷在青石板下。春天的傍晚,放了学,找一个陶罐系上绳子,扔进门口的水塘,第二天天刚蒙蒙亮,轻轻地把它拉上来,罐子里就会有一两只桃痴傻乎乎地在游动,倒有几分处变不惊的风度。记忆中,童年快乐的一天便开始了。
有时,一夜春雨。清晨,稻田里的水会哗哗地从缺口流向沟里,水入沟中的交集处有鱼噼噼啪啪地戏水,一群群,争先恐后。这时,我会兴奋地去“捞田缺”。斜风扫雨,触面微凉,也不撑伞,戴一斗笠,持一捞兜,赤着脚一个秧田一个秧田地奔波,蹲守,捕捞。看着一条条银光灿灿的鲫鱼在我的网兜里活蹦乱跳,自己仿佛也成了一条鲜活快乐的鱼。也有的鲤鱼或鲫鱼,体力足,冲劲猛,顺着田缺流水的小瀑布,错把秧田当龙门,跃进田头,便是真的“虎落平阳,龙搁浅滩”了,过几天放水烤田,它们就永远告别了那一汪清澈的沟水。这个幻觉中的龙门,纵使它们为此付出千百倍的努力,依然成了跃进死亡的地狱之门。
汛期以后,会出现伏旱,内河的水位下降很快。这时,圩管会便会打开陡门,把水阳江的水放进圩内抗旱,一些江里的鱼,随着汩汩的江水就涌进了沟中。最多的是针鱼,一条条圆白修长的身躯,挺着一杆细如松针的银枪,成团成团地贴着圆圆的月亮快乐地在水中巡游。暑气微漾的夜,母亲会带着我,划一只小船,把马灯摆放船头,缓缓地向前。一丝丝清凉拂面而来,母亲一手扶着马灯,一手用插网迅速地朝水中插下去,哗啦一声,月亮碎成了一粒粒珍珠,十几条小针鱼被捞进了船舱,噼黎吧啦地跳着……待月儿又圆了起来,发现前方又有成团成团的针鱼在缓缓地游。
小餐鱼喜欢在每家每户的水挑上聚集,吸引它们的是饭后洗碗所飘荡的油水。这是我们钓餐鱼的好地方。用一根缝衣针放在煤油灯上烧热,稍稍用力就刖成了一个鱼钩,串上尼龙线,找一根鹅毛杆子作漂浮子,绑上一根小竹竿,再在大水牛身上打一些苍蝇,装在空火柴盒中,作诱饵。钓钩向着成群的餐鱼甩去,它们会争先恐后地咬钩,飞快提杆,一道银光闪离水面,朝着岸边竹篮一抖,一条餐鱼就成了篮中之物。又钩上一只苍蝇,向鱼群甩去,又是一条银光飞进篮中……那时的暑假,总有大段的时间是在这样有趣的垂钓中度过的,真是莫放暑期佳日去,最喜水中餐鱼来。
那些鱼,伴我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我简直克制不住这份情感,曾试着为它们写过一首小诗来怀念:
滔滔浊流的长江
曾是鱼儿辟波斩浪的故乡
在一个雨季的黄昏
水阳江里曼妙的浪花
献给了这些浪迹江湖的鱼群
它们顺着长长的滩涂和堤岸
逆流而上
游过了一个春天的桃花汛
又游过了一个梅雨季
没有在水牮头的漩涡中逗留
也没有躺进南漪湖的九嘴十八湾
这些鱼
不再思念长江的澎湃宽广
也不再眷恋那惊涛骇浪的青春张扬
虽然那里有一道道可以去跨越的龙门
虽然那是一个广阔的地方
汛期过后,旱季来临
它们护送着水阳江汩汩的清水
穿越陡门,来到了圩乡的沟渠
那些温暖的水
有的被抽进了农田与禾稻为伍
有的在清澈的沟渠中邀来了清风和明月
也许是崇敬天空中那轮皎洁
也许又喜欢水底下这片静溢
一个满月的夜晚
我发现那些鱼在月亮上游弋
从此,每天都等待着
有这么一个圆月之夜
……
小餐鱼和大白鲳长得很像,看起来像孙子和爷爷的关系,但它永远长不到大白鲳那么大。大白鲳喜欢集中到中垾的大坝头繁殖,那是圩乡下坝最大的一片垾子。春雨哗哗,垾子里的积水,汹涌地汇集到那个大排水沟。在这水平如镜的圩乡,终于有一股水流带着巨大的冲力倾泻而来,鲳鱼们久违的野性被激发出来,它们喜欢这种有力度的较量,迎着这一股浊水逆流而聚。对于这些白鲳,是走向激情燃烧的快乐,有的也是游向危险的灭亡。那时,没有休渔的概念,周围的大人小孩,也鱼汛般蜂拥而至,赶一场捕鱼的盛宴。雨霁天晴,彩虹在东边搭着一座漂亮天桥。大沟边,有的用鱼叉,有的用旋网,有的用抛钩,虎视眈眈,各展才艺。更多的人是站着那儿呐喊,看到有人戳到一条大白鲳就不断地喝彩。也有的干脆划一条小船,横漂在沟心,等待鲳鱼自己跳上来,大有姜太公捕鱼,愿者上船的风范。直至西边的红烧云燃尽,成了一片灰幕,月儿已悄悄地越过了树梢,热闹的捕鱼竞赛才渐渐地结束,大家各有所获,披着月光尽兴而归。
圩乡最珍贵的鱼当然是鳜鱼。“桃花流水鳜鱼肥”,它一身华服,斑斓多姿,又称“桃花鳜”。捕鳜鱼有一种方式——放鳜鱼笼子。鳜鱼笼子是用竹篾编的大竹篓,圆柱形,两头有口,口中有竹篾作为倒刺,鱼能进,不能出。遍身缠附着长长的杨树气根须,放在离沟底约一尺许的半水中,等着鳜鱼自行入瓮。鳜鱼的漂亮和它的判断力并不成正比,它常把这种笼子当成它的窝,就顺着口子挤进笼中,所谓“鳜鱼笼子,只进不出”,进去后,只能呆呆地呆在里面,等待放笼子的来“解救”。放鳜鱼笼子要有一杆竹杆做支撑,也是标识。那时,鱼塘是公社的,竹竿隐于水中常被巡塘的发现。按说,鳜鱼是一种野生杂鱼,处于食物链的顶端,塘中越少越好。可私自放笼子一被发现还是会被割了“资本主义尾巴”的。
清风和蔼地抚摸着村庄,月光慷慨地洒向沟水,根海哥带着我轻轻地划着小船悄无声息地来到沟中心的红旗下。根海是放鳜鱼笼子的高手,他知道越是危险的地方越安全,就大胆地把笼子放在红旗的旗杆下——那是公社副业队插在塘里的标志,是权属的象征。副业队的职工万万没想到在他们的红旗下就有一个“盗挖社会主义墙角”的鳜鱼笼子。过两天,趁着月光再去拉出水中的笼子,哗啦啦一片,闪着金黄的光,大大小小的鳜鱼有四五条。
圩乡没有专业渔民,但掌握一两门捕鱼技艺的还是不少。一般是以家族来传承的,爷爷带孙子,叔叔带侄儿。每一门技艺都是有那么一点窍门,一技在手,吃饭不愁。但没见过那一位捕鱼高手像真正的手艺人那样开门收徒的。
张卡钓算是一种较为专业的活儿,有一定的技术含量。卡子是用竹丝修剪的,修钓子要精细,讲究挺拔,所谓“弯而不折,挺而能伸”,有韧劲。煨小麦也不能马虎,不可太熟,太熟了绷不紧,被水一浸就散了。又不可太生,太生了卡子插不进去。卡钓是在家中一盆盆地把小麦装好,堆在盆中像一座小山。到了沟里,一人划船,一人在船头放钓子,“山”尽盆空,一面垾子就绕过来了,再换一盆。一天几条沟,晚上放钓子,清晨去收钓子,轮着来。鱼在水中一咬小麦,极富弹性的卡子就绷住了鱼鳃,它怎么游也逃不走了。
卡钓张的最多的是鲫鱼,有时也能张到鳜鱼或黑鱼。鳜鱼和黑鱼是不吃小麦的,那是它们把已被卡了的小鱼不假思索地当活食吞下去了。在圩乡的水族中,鳜鱼和黑鱼是绝对的强势。可强势有强势的利益,强势却又多了一份危险。吞进肚中的小鱼是吐不出来的。任凭它们怎么挣扎,就是拽破肠子也挣脱不了那一根细细的卡线,只好乖乖地等收钓人来收拾了。这叫“吞子”。
有的鱼吃了卡子,就在水下面的水草上打转,绕了一大圈的水草。此时直接拽,一用力,鱼一挣扎,就逃了。要用锯镰刀伸进水下,把那一团水草疙瘩割断。包着鱼的那一片水草就浮了上来,用捞兜一捞,青绿的水草丛中一条白花花的鲫鱼,“啪”的一声,就掉进了船舱。我的小婶家就是张卡钓的,小时候家里姐妹多,出生不久就由她母亲带在船上,一次她睡在船舱,被父亲不小心踩了一脚,也没到医院看医生,从此身体一直病歪歪的,在众多姐妹中她长得最“细心”,家里素性叫她“小小”。前年,我的小小婶还是因病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圩乡有一种大小一扫光的捕鱼方式叫抄抄网。每年年底起鱼时请来抄抄网的,在沟里下好几道网,安排人在两岸一道道地往前拖。一条大沟从下网到刹网要半天时间。沟里的鱼被静静地拖到终点,快刹网时,网兜面积越来越小,那些心急的鱼就开始在网中飞跳。特别喜欢跳的是鲢鱼,俗话说“三个鲢子满塘鱼”。有的虽然跳出了第一道网,却还是落入了第二道网内。大部分鱼不论大小都被一网打尽。特别是是浮于水中的胖头鱼、鲢子鱼和大白鲳,几乎可以抄绝。一网能网到好几百斤,算是最毒的一种捕鱼方式了。当然一物降一物,也有漏网之鱼,像团鱼、黑鱼、大青鱼等这些底层鱼,它们或钻进了鱼洞或躲进淤泥中,往往能躲过了抄网的包抄。
一年中秋,长池里请来了抄抄网的,在中途下网,抄了半条沟。哪知刹抄时竟然有一千多斤胖头和鲢子鱼,一条条白花花的鱼装满了一只船。我们几个小伙子就想做一笔生意赚点钱,一下子买下来,准备划船到高淳市场去卖。半夜,一轮圆月悬挂高空,照着大沟亮如白练,大家划船出发了。到了圩埂处,把在箩筐中的鱼一担担地挑过圩埂,再把船拔过大堤放到水阳江中,又把一担担鱼挑上船。在江里划船,大家更加用力,正好是丰水期,江水滚滚而下,一不小心满载的小船就会有翻船的危险。到了永丰圩的一处陡门,找到了一个较低的埠头,把船拔到了圩内,又是一担担地把鱼挑过去。终于在天亮之时来到了高淳的新桥头。新鲜的鱼,加上又是节假日,我们的几担鱼很受欢迎,买鱼的人蜂拥而至。我们高兴地称鱼的称鱼,收钱的收钱,不到半个时辰,全卖光了。刚要收起稻箩往回赶,一位戴着大盖帽的中年人抓住了一位同伴的秤杆,严厉地说:“谁让你们不进市场的!快把税交了。”
“同志,我们这是自己家的鱼,不是做生意的。”同伴中有人向他低声地求情。
大盖帽一脸严肃,从包里拿出现成的税票,刷刷地往下撕:“一张十元,五张五十元。”
同伴无奈地递过去五十元,取回秤杆。大家回到船上一算账,赚的钱刚好交了税,算是白忙活了大半夜。年纪稍大一点的木生说:“还好,没亏本。”
于是,大家又嘻嘻哈哈地划起小船往回赶。
长池是一个千年未曾干过的塘。在干旱的年景,它的中心都有深不可测的清水。传说垮塘心有一条大鱤鱼,每当梅雨季节,天气作闷,它就会浮上来,黑压压的,一大截,像似沉未沉的小木船。有一天,章士大爷从雁翅街上喝过酒,沫着若隐若现的月光划船回家,过了和平桥,突然船撞上了一道“坝埂”。他自言自语道,怎么多了一条坝呢?就下船,把船从坝上拔了过去,重新上船。刚要划船,只听船后哗啦啦一声,犹如雷鸣,定睛一看,好像是一条大鱼沉下去了。后来有人问他是不是有这回事,他却是避而不答。
今年回家倒听说有一个专门钓青鱼的垂钓者,在这条沟中钓起了一条七十二斤重的大青鱼,像一条小鱼鹰船一样。为了钓这条鱼,他几天来一直在用玉米粒喂饵料,把所有的吊钩都放大尺码,耐心地等待了几天。后来又在这里钓了几条六七十斤重的青鱼。沟下的世界真是神奇,这些鱼也是这条沟的主人了,它们经历过捕鱼人的丝网、抄网、旋网等各类网具的威胁,身经百战,躲过了无数的劫难,可今天却还是没有躲过这美味饵料的诱惑,终于离开了这片水域。我相信水下仍然有像它们一样有生命力巨大的青鱼在那里坚守,它们应该是这条沟的灵魂。
每年秋收之后,农人除了挑圩基本上没有什么活儿,圩乡农家有“半年辛苦半年闲”之说。此时柴干米老,自给自足,杀猪宰羊办年货,成为乡村生活常态,真可谓,“村村沽酒唤客吃,并舍有溪鱼可叉”。生产队也会把村前的烟火塘用水泵抽干,竭泽而渔,分给各家各户作年货。
干塘的那一天,大家纷纷带着渔具来捉鱼,那是真正的捕鱼狂欢。捉上来的鱼,摆在生产队的稻场上统一分配。生产队队长把鱼一堆一堆的分成二十堆。会计写出“1”至“20”的号头,一张张贴在鱼堆上。然后再做二十个阄,折起来,放进一个搪瓷脸盆中。大家轮流着去捡阄,拆开是“1”,就去拿1号堆的鱼,捡到“2”就去把2号堆的鱼装回去。虽然鱼堆的鱼也有大小多少的差别,但大家毫无争议,认号取鱼,“好汉阄上死”。这就是朴素的按规则办事,没有谁发现自己的鱼比别人的少一点而反悔的。现在想来,这种分鱼方式,就是在西圣哈氏看来也不失为公平分配的一个社会学经典案例。
如今,行走圩乡,白云依然悠悠地飘荡在上空,脚下的那块土地依然肥沃而坚实,只是圩乡的水,不再像过去那么清澈。我常想,现在的那些鱼儿,比起它们的祖辈,一定缺少了明月之夜一次快乐的游弋。圩乡的少年,比起我们,自然也少了一段有趣的时光。
宋代诗人周邦彦曾任溧水知县,一日闲暇,来到相邻的圩乡水阳游玩,为我们记录了当时圩乡人的捕鱼情景:“清溪在三阙,轻舟信洄沿。水寒鱼在泥,密网白日悬。水阳一聚落,负贩何阗阗……”极目所见,诗人的描绘,有的已渐渐走进了历史的深处,有的仍风物如旧,有的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可,我还是很怀念那一片灵动的水,在微风轻拂的夜晚,拥抱着水底一轮清澈的明月,让那些可爱的小鱼映着月光在水中快乐的游弋……
作者简介
时国金(笔名清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宣城市作协主席。作品发表于《钟山》《清明》《中国铁路文艺》《安徽文学》《文学港》《诗歌月刊》《西湖》《太湖》《青海湖》《散文百家》《人民日报一大地副刊》等报刊。有作品被《散文海外版》等选刊转载。曾获首届、二届羡林杯生态散文大赛一等奖。散文集《此心安处是圩乡》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