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4-05-27 来源:安徽作家网 作者:安徽作家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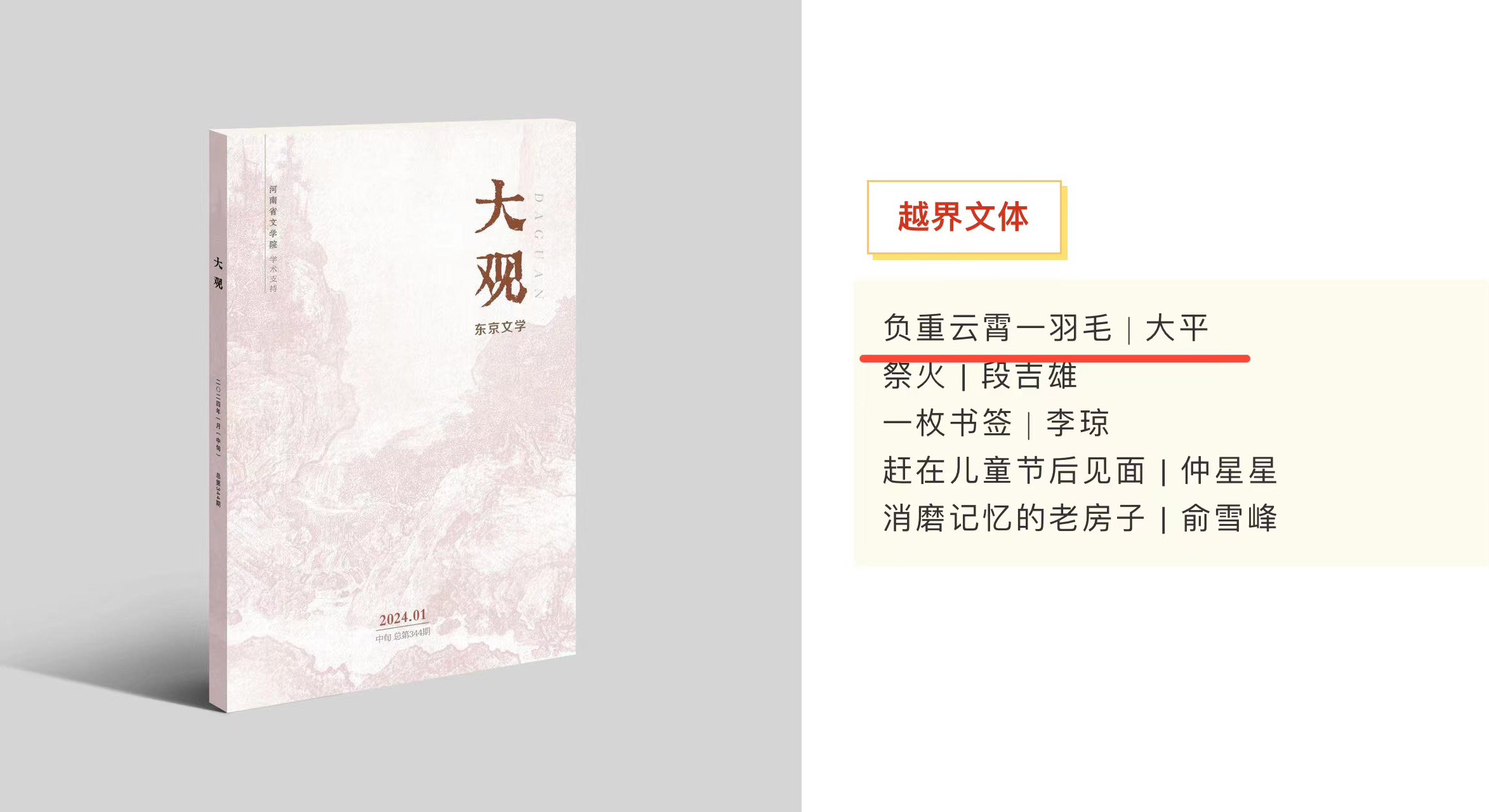
作品欣赏
负重云霄一羽毛(节选)
胡大平
一
初冬,货卖不动。小店四壁萧然,又满目琳琅:钢丝网,插片,出样方管,站架,撑架,塑胶模、头颈半身模、无脚模特。武汉进的夹衣两用衫挂着,走不动,又进了长袖花裙和风衣,被客户打回头,只好又进些化纤薄袄,走了几件——妻子说像她吃药产生抗药性一样。
我只好背包出发。嘉兴长途站出来,一个拾垃圾人为我指路:“你别再进站买农班车票,也别往街头公交站跑了,只须向北转个弯,看见一个配图为粽子类的广告门头,只管往里走,就有开往平湖的160路车。”他是个明白的乞者,我是个迷途的商人。但我耳朵里装着王步高先生的音频《唐诗鉴赏》,嗓音尖细,沙哑,苦口婆心,有点像患甲亢的老年女声,歌吟屈原和汨罗江。粽子在浙江早超越了舍身护尸(诗)的功用,成为一种四时皆宜的全国性副食。我仿佛看到此刻北京武汉乃至郑州西安街头也有它们的身姿,在未凛冽的天气里冒着咸甜袅袅热气,待温暖人们的胃。眼前“沙县小吃”等闽食,在越地几乎姓嘉了。店堂也供应粽子,跟隔壁“真真老老”“五芳斋”卖一样的东西。两种地方的铺子,贩卖一样的吃食,这是个单调,趋同,而繁华的世界。
浙江人号称中国的犹太人,总能把跟他本没多大关系的东西,做大做强甚至永久落户。如互联网大会,淘宝马云,如我此行之目的地。公交车像给婴儿“摇窠桶”沿途不断停靠,总有十数站,我打听中国羽绒城,司机瞄我一眼,拎起个蓝色路牌敲着有些怀旧地说:它原来是161路,可送你达目的地,但现在……现在我上了一辆黑色杂牌小汽车。司机小苏和我们同下“平湖北”,他走向一辆冒着浓浓尾烟等侯他的坐骑,我一看竟挂牌“皖G”,他乡遇故知就搭了便车。身边新修的细黑颗粒的柏油道旁,惋惜剩下四位北方口音的美女,各人拖一只粘满飞行托运标的大号拉杆箱,我们盛邀同行,伊们迟疑了下,便微笑摆手说:“队伍太大啦!”四支刚点着的又细又长的女士香烟,像四只小烟囱在冬风里拉风。郁达夫坐车去南京,途中挥别美女惆怅地送祝,只能送伊们到此,我要先下车了,伊们的美丽从此与我无关。我发此感叹。小苏说这有啥?北方女的不抽烟男的会不要的。
歧途百里而来,好像就为邂逅。在嘉兴她们与我先后上公交,拖着比身体大几倍的大箱子,上来就问:中国羽绒服大市场怎去?她们中一位下巴略有点“尖嘴”的,挨我坐下,说帅哥让我靠窗好么?我礼让说好。再坐下感到芳邻开窗的一点风,和她身上有股烟叶的微臭,和淡淡芳香。
她们辗转乘飞机而来,如我一样出来找“食”的?秋尽江南草未凋,到年底也只剩两三月了……她们动作的洒脱,作风的泼辣,透过她们轻寒的衣衫,也能感到为了营生而奔波的倦意与疲态。
二
不到三点钟,“中国羽绒城”都是缤纷络绎的顾客面孔。这是座无檐无遮,高级冰箱样式建筑。它的银灰装饰,促人想添衣保暖的色调,我没太在意,倒是“中国”等五个小汽车大的字,增添了日进斗金的喜感。让我觉滑稽的是,走进大门,却见一众“高人”踩着高跷,有如过江之鲫,一溜溜摇头摆尾地游进游出。难道我走进《山海经》大人国了?这类“高人”在常熟马路上我偶尔领教,为之捏把汗,一不小心碰出个“高级”车祸啊。王步高先生在我耳畔说: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一圈儿逛下来,觉得是找着富矿了。满眼新意,举目春风,心情一激动,马上微信妻子:找到小姑娘,我还想亲近老太婆吗?妻子即回:呸,你还做梦找小姑娘啊……她说正在修电瓶车,准备接娃“放学”,两个孩子上托幼所。我们天命之龄,前年先有了孙女,又得个小儿,如何不喜?然而喜忧参半,要挣钱养活啊。我忙解释,大概不用跑武汉找老太婆棉袄了,以后咱专做小姑娘羽绒服。店里的积压,秋衣卖不掉,冬又来了,十月小阳春,街头的大娘和阿姨们有的还潇洒学年轻人穿着短袖衫,摇扇跳舞。实体店就是夫妻店,夫管进,妻管出,我做老板她当伙计,她做老板我当伙计。进市场顾客少,进店门的更少,同行又竞争,都恨不能像“招客女”动手拉破他们的衣裳——希望进一件我们的衣裳。百思无计,多方打探,得知南国有俏佳人——浙江平湖的好羽绒服,质优价廉,我觉得是找着啦。
市场好好一转,到傍晚出来时,只见西斜的太阳黄黄脸在“冰箱”楼头欲坠,仿佛也须保暖添衣的样儿——几十亿岁的老头还怕冻死吗。广场,地砖,大理石,马路牙,小摊子,一些小贩们都出来吆喝了,搞出油滋呵啦的诱人香味,是勾人馋虫的香和味。我走过去想买串填个肚,炸好的、存量的却觉得不放心买。在一个戴穆斯林帽的新疆汉子炉前,竟有几个“高人”,攀过了我的头,足蹬平衡车立等,紧盯着冒烟的微红的炭火,飘着孜然香味的各种动物肉。我吞了几大口口水。广场溜光的大理石地面上,“高人”潇洒转圈,如古人打马蹓弯儿。广场大理石延伸的尽处是一片池塘的坑洼,栽植的新草稀而瘦还有点像黄毛丫头,真是农业与工商业的交相呼应。想不久前还是农家门前的水宕,也说不定还有大片谦虚勾头的稻田晚稻棵子,只随着羽绒城及箱包城的落户,家禽包括鸭子和鹅都不得不摇摆着屁股,洗脚登岸,幸没做了明炉烤鸭或烧鹅吧。过马路找家兰州拉面,我落座“喝”了碗稀汤的西北烩面。不知啥好刀工切的,牛肉薄似新款的粘胶羽绒绸面料,红汪的辣油却极舍得,盖满碗头,我只吃个三分之一饱。
天渐黄昏,有冷露悠悠降,我背包打听旅馆。
三
客店名拗口,入住了想躺会,后窗传来几声狗吠。仿佛它们是和我的肚子一样饥饿咕咕地叫唤。冲了澡更睡不着,便下楼逛街。有八点钟了,摊子们却还点着小小的灯,如豆如烛,货物简单,人物简单,多是些女摊主,看守着清一色的捆着受刑的柚,和带叶散乱堆山的橘。潜伏在我耳朵里的王老师,犹然女声般高吟:“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唐诗鉴赏》也提到苏东坡,坡翁曾做杭州通判,此地距“天堂”仅百里之遥。人烟寒橘柚,并不便宜,我只问问价走开了。
夜色黑寂,街头冷清。《平湖秋月》是曲也是词,手机上存的纯音乐,无歌词,聆听倒生出“杭州作汴州”之感。此地江南,平湖小县,离江不远,距海亦近,何因何故,满街男女,饮食风情尽富含北国气象?不觉逛到个“丫”字形街道路口,三个方向可选。淘汰掉许多烤串吧,寻着一家“阳春馄饨馆”,江南味的大个儿,苏州味的馅儿,把几只硕大温暖的错季馄饨落肚,才觉爱了此夜。
此地的狗不肯我睡,它们在后窗外,声震屋宇,三更不歇。披衣爬起去看,窗外是一大片死寂的荒漠,朦胧月光下可见许多烟囱般,化工厂式的两人合抱不下的粗大管道,横空而过,弯弯曲曲,不知输送着什么。难道是暖气?这个冬夜有多少人等候着这温暖,尤其我这外乡人,来此寻“食”者。狗的吠声,它们狺狺的叫声,是在战斗,在夜色中更显凄厉,具有性别和派别区分的,既张扬洒脱,又粗野鲁莽,然而合唱的尾声部全是失败的悲壮与苍凉。“汪呜——汪呜”,似失恋者的啜泣狺狺。苏青挨了丈夫打,赌气离婚,寄居到姑父家,想念孩子。她生了一堆娃,夭折后还剩俩。她把孩子接回自己带,无职无收入,拿啥养活呢?她想嫁掉自己,有天晚上情人如约半夜过来,进屋脱鞋摸向床,看到一地的孩子,一地生活着的小裸肉。我想起张爱玲《我看苏青》里说:“数不尽的一点一点,黑夜里,狗的吠声似沸,听得人心里乱乱地。”想起家中向南的窗口,有一盏如豆小灯点亮了,凌晨一两点,妻子醒了,因为孩子醒了,哭,她要喂奶,她要把尿,拍哄着睡下,天不亮又要赶往店里,开门,出摊,迎客,忙得饭都顾不上吃,又愁得饭都吃不下。此刻她胃疼发作么,怕弄醒娃,拧小灯,爬起吃药。人活着,药和饭都要吃,因为人要活着。好在我已找着食源了,羽绒服定能打通一线商机。
窗户关上,嫌闷嫌憋;打开,狗叫并蚊虫,如雷灌进。
“邑犬群吠,吠所怪也”。韦中立要拜柳宗元为师,柳说,庸、蜀的南边,经常下雨,很少出太阳,太阳一出来就会引起狗叫。“仆来南,二年冬,幸大雪逾岭……数州之犬,皆苍黄吠噬,狂走者累日,至无雪乃已。”我不能做你的老师,韩愈已做了蜀地的太阳了,您又想使我成为越地的雪吗?
此是越地吗?今夜无雪,我只好,只能,只有用王步高先生的细高音,去对抗窗外的众犬高歌。它们的歌啸,使我无以入睡,欲微信与妻子温存几句,但明白还是不要惊扰她和儿的辛劳之梦,只好拿被子包住脑袋。可是仍能听到一只似中壮年的母狗,连连高唱三四分钟不歇,觉得她有点上气不接下气了,我心疼地想,她总要换口气吧。她似乎真累了,歇约两三秒钟,又一阵尖锐如撕布裂帛的“啸嗥”响遏云霄而来,这一家伙便是五六分钟——半个世纪的行程,我觉得被她“啾啾”地送入万古荒野,并抛上了云端。终于她息歇了半分钟,我心里祈祷,好了好了,来不及捂耳,破壁又冲进来一片嫩狗的杂声, “哇哇哇哇”地嗷嗷待哺。
作者简介

胡大平,安徽枞阳人,中国作协会员,鲁院安徽作家班学员。有作品发表于《山花》《安徽文学》《北京文学》《飞天》《黄河文学》《湖南文学》《散文》《星火》《雨花》《天津文学》《阳光》等。出版小说集《火辣阴森的正午》《蛇》。